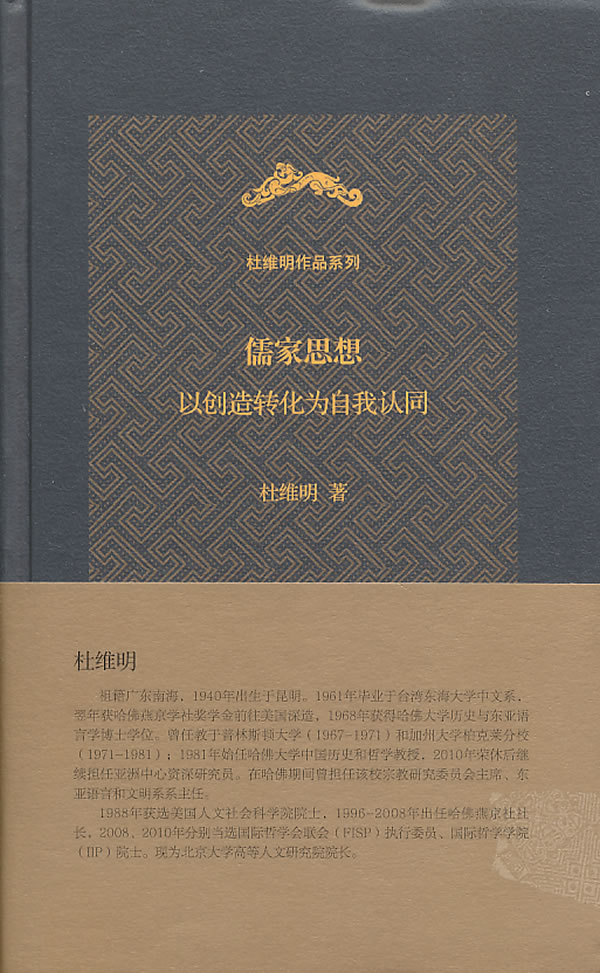儒家学术从以《五经》为核心经典体系的汉学过渡
◤为了应对当代中国面临的现代化、全球化挑战,如何进一步弘扬中华轴心文明的价值和智慧儒家学术从以《五经》为核心经典体系的汉学过渡,吸收其他文明的思想成果,从而建构一种新时代的思想共识,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是我们面临的一项最重要的文化建设课题。探讨《四书》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关系,对当代中华思想文化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是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早期儒学重要著作,它们是早期儒家学者在继承三代文明的基础上,对时代精神与社会问题的学术思考和解决方案。这些著作对人性与人生意义、社会与国家治理等方面的思考具有恒长价值与普遍意义。两宋时期集中体现儒家教育哲学思想的着作是,宋儒将这四部典籍辑合成为一个整体——《四书》,并对这些典籍作出重新诠释,使《四书》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学术体系,故而进一步推动了儒家思想体系的建构,《四书》亦因此成为儒家学术体系中的核心经典。这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从以《五经》为核心经典体系的汉学过渡到以《四书》为核心经典体系的宋学。此后,《四书》在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领域均产生巨大影响,标志着中国古典儒家文明转型的完成。
儒学体系的三种学术形态
首先,从学术思想的源头上,探讨《四书》的早期学术形态,即以《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作为儒家诸子之学的思想特点来考察。
儒学体系体现为六经之学、诸子之学、传记之学三种学术形态,并各有其思想特点。《史记》提出“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儒家是通过学习、效法“六经”中先王的思想,继承三代的文化传统,才创立了儒家学派,并建构了《六经》的经典体系。《六经》是三代先王之政典,主要记载上古三代的礼乐制度,其学术旨趣在政治秩序的“治”。但是,早期儒家又开创了“六经以外立说”的子学体系,《论语》《曾子》《子思子》《孟子》记载儒家诸子倡导的仁义道德,其学术旨趣在价值体系的“道”。《六经》与儒家诸子不仅仅是文献类型、学术形态不同,更加重要的是这些文献的思想主体不同。“六经”以三代先王为思想主体集中体现儒家教育哲学思想的着作是,而儒家诸子以儒家士人为思想主体。思想主体的差异导致思想旨趣的重大差异,六经原典以“治”为目标,而儒家诸子则是以“道” 为目标。《六经》原典记载三代先王治国理政的政治经验和礼法制度,儒家诸子的《论语》《曾子》《子思子》《孟子》等是儒家士人集团针对春秋战国历史时期的现实政治、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系统思想和治国方略之作。
六经原典与儒家诸子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区别,故而儒家需要将二者的思想整合起来。儒家学者早就发明了一种将六经和诸子经学结合起来的学术形态,即“传记之学”。儒家学者通过“传记之学”,将六经之学与诸子之学整合为一个有机的儒家思想体系。这样,儒学既能够保留深厚的文化传统意识,又具有开拓的思想创新精神。早期儒家通过礼学、仁学的相互诠释,实现《六经》与儒家诸子的思想互补。同时,六经之学与儒家子学之间存在一些差异,故而《六经》的礼学与《四书》的仁学又存在明显的思想张力,这些差异与紧张可能引发儒学的思想纷争与学派分歧。
西汉希望解决周、秦两种制度和文化结合的问题儒家学术从以《五经》为核心经典体系的汉学过渡,故而在政治制度上实行秦制,而在文化上推行以西周文明为典范的《五经》之学。汉唐《五经》学思想传统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帝国政治的礼法并用、王霸杂之的“帝王之学”。所以,汉唐经学推崇《五经》学,无论是发挥《五经》学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还是注重《五经》学的名物制度考据的古文经学,其主导目标都是直接为帝国政治服务。
《白虎通义》就是东汉完成的一部儒家经典与帝国政典结合的大典,体现出儒家士大夫与帝王在合作过程中成型的文化共识与政治盟约。作为一部汉代帝国政治的政典,《白虎通义》的根本目的是确立帝国的政治制度、治理原则、礼乐文化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原则,突出地表现出帝国政治的要求。作为一部儒家经学的大典,《白虎通义》通过大量引证儒家经典来表达士大夫的政治思想与文化理念时,采用的是汉代士大夫的思想表达。
追求“内圣之道”提升了《四书》学的地位
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变革,引发宋儒对《四书》的特别重视和重新诠释,由此推动中国思想传统的重建。宋代士大夫群体作为文化主体力量,主导了一种新型儒学的兴起和发展,终于形成了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宋学。宋学是一种新型学术形态:它既强调回归传统经典,又追求思想创造;既追求现实政治功利,又向往超越性宗教情怀。宋代士大夫通过对唐宋学术转型的推动,创造出崇尚“明体达用”“内圣外王”“义理之学”的“宋学”。
宋儒从儒家经典中阐发义理,一开始就包含着创通经义与革新政令、世道人心与经邦济世的双重目标。宋学思潮中的不同学派学者均在强调自己的学术是一种“明体达用之学”“内圣外王之学”,以解决历史上的人心世道、经邦治国的现实问题。
但是,自从熙宁新政失败以后,宋学明显开始内圣化的演变和转向。后来的士大夫越来越强调内圣之道的重要性和根本性,认为必须首先解决道德思想问题,才可能实现国家治理的目标。
先秦儒家价值观为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奠定了基础,宋代《四书》学对先秦儒家核心价值观作了进一步的思想提升。通过挖掘《四书》中的忧乐情怀,宋儒找到了儒学及中国哲学的深层精神。他们还进一步对《四书》作出创造性的诠释,将《周易》的宇宙哲学与《四书》的人格哲学结合起来,建构出一种超越精神的内圣之道和天人一体的性理之学。通过对“四书”的创造性诠释,他们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原本就有的“仁义”“中庸”“修身”作出了新的理解和发挥集中体现儒家教育哲学思想的着作是,使得这些儒家价值观念由人道上升到天道,重建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孔子提出了作为“礼”之依据的“仁”,但是“仁”要能够成为普遍性行为准则,还必须表达出必然性的力量。宋儒确立《四书》的新经典体系,其学术使命就是要重建“仁”的形而上意义,以确立“仁”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宋儒通过对仁学的诠释与建构,把《四书》的心性仁学与《周易》的天道仁学结合起来,建构出一种天人合一、体用圆融的新仁学。
在早期儒家典籍中,中庸之道主要体现为一种实践性智慧和德性,所谓“中”明显具有知行一体、主客互动、天人合一的思想特点。宋儒《中庸》学的突出特点和重大贡献,就是以“理”诠释“中”,对原典的中庸之道作出了以理为依据的创造性诠释。宋儒以“理”诠释“中”,故而能够从知行一体中拓展出知识理性,从主客互动中拓展出主体精神,从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建构出天人一理的哲学体系。宋儒通过对《中庸》的一系列创造性诠释,推动了儒家中庸之道的思想创新和理论建构,使中庸之道的哲学意义得到进一步提升,《中庸》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经典。
宋代士大夫不仅推动了儒学重建,他们作为“道”的承担者和主体力量,还积极致力于道统论的建构。不同于《六经》以先王为主体的道统论,宋儒的道统论是以士大夫为主体的。为了弘扬儒家士大夫主体意识,宋儒《四书》学解决了下列几个问题:在儒、佛、道三教并盛之时,只有儒学才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在儒学学统四起之际,对《四书》的正确诠释才是儒家正统;在道统与政统的关系中,必须由道统主导政治秩序。宋儒建构的道统论鲜明地表达了宋代儒家士大夫的主体意识。(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点击“了解更多”获取全文)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