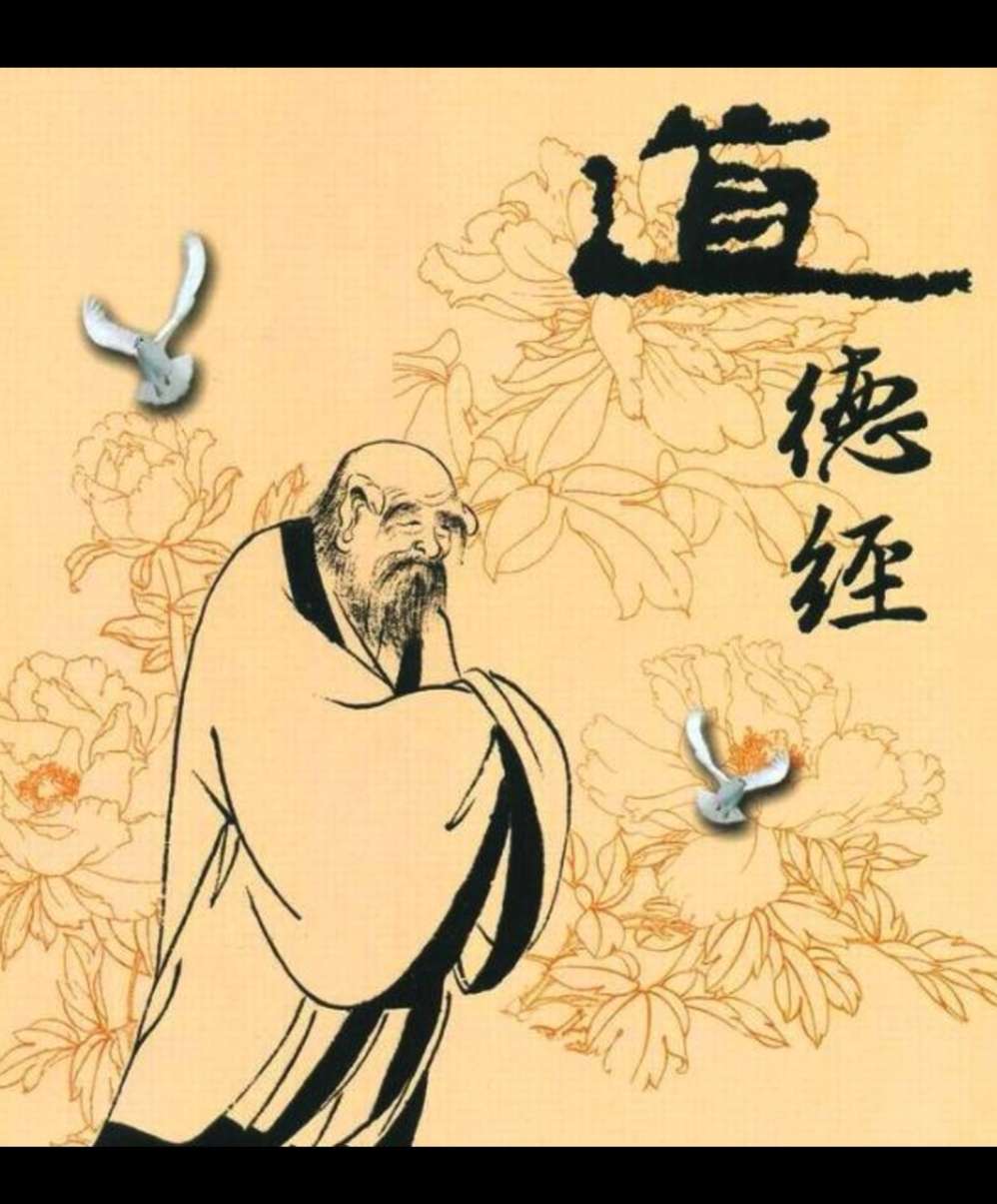:一种是企图延续朦胧诗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让西方文化进入中国,朦胧诗是这一时期在诗歌领域的反映,同一维度的小说领域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出现。八十年代中期的“现代诗群体大展”,让第三代诗歌以几十个流派的规模,呼啸着来到《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的“聚义厅”,他们众声喧哗,参差不齐地向朦胧诗发出了另立山头的呼唤。以“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非非”“他们”“莽汉主义”等流派为代表,提出了“反文化”“反崇高”“平民化”的口号,在语言上呈现了“去隐喻”“口语化”的美学特征。在第三代诗歌运动中,出现了两种重要的写作倾向:一种是企图延续朦胧诗“东方现代史诗”的写作,挖掘民族原始生命伟力的,以及与巨大文化原型、先民生存景象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宏大叙事,这些都在后来的写作实践中被逐渐遗弃了。表面看是因为这种写作流于空疏、晦涩和不及物:一种是企图延续朦胧诗,以及他们所重视的文化原型对当代生活的疏离而被遗弃的,本质上是因为这种写作的历史整体观、民族整体观和国家(东方)整体观与时代逐渐觉醒的个人主义、人文主义相冲突所致。另外一种是在西方现代主义和模棱两可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下兴起的个人写作。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个人觉醒和社会生活中对个人生活的重视,倡导平民化、日常化和口语化的诗群和诗人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接受儒家佛家道家高语境文化,并被后来的写作者所继承,成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重要成果。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崛起,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诗歌的现代主义转型,同时也建立起以个人观照时代,和以个人主体意识观照社会生活的具有自我深切体验的美学原则。以个人觉醒替代前现代的集体意识,这在哲学上既应对了哈贝马斯的修正的现代主义对洞察世界的深刻性追求,也符合福科、德勒兹等人对个体、边缘、少数民族等等的尊重的去中心化、平面化的后现代主义观念。
然而,我们意识到,第三代诗歌运动以来的诗歌写作,虽然个人主义写作已成为当代诗歌写作的圭臬,但个人内在精神的匮乏和羸弱,却极大地制约着当代诗歌的成长,可以看到我们的诗歌所创造的世界形象依然是那么的矮化(乡土中国的国民性气息)、弱化、扭曲化。与世界的诗歌格局相比,我们的诗歌还处在胡同和某地的旮旯里,诗歌作为个人主义的产物而人的形象还没真正树立起来,与现代人可能建构和呈现人(生命)的可能性相去甚远。这归根结底是我们个人主义文化内涵的匮乏和民族性格中逃避冲突的生存策略使然,没有更具人类意义的文化充实到我们的个人世界里来:一种是企图延续朦胧诗,以及面对社会生存困境的勇气。
先请大家来看看第三代诗歌运动以来颇有影响的几位诗人的作品吧,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诗歌所葆有的文化内涵是什么。
于坚的《尚义街6号》,以写实的手法,呈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群年轻人在尚义街6号混乱不堪或者说貌似生机勃勃的青年生活,其实这背后支撑着的是八十年代的“阿飞文化”。“阿飞文化”属于当时的一种亚文化,以迪斯科、抽烟喝酒、录音机、喇叭裤、自由恋爱、同居等作为文化符号和行为艺术,对抗原有的社会秩序、规范,以获得年轻人的存在感。有些人那时也许觉得,即使他们处在犯罪的边缘,却也因此有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感觉。我当时就在家乡的宾馆舞厅,看见一个时髦的小阿飞在舞曲的间歇朗诵他即兴的诗篇:“当警笛响起,霓虹灯在闪耀,我独自走在无人的大街,风,向我冷冷地吹……”这朗诵赢得了女孩子们在尖叫,令我佩服的情感和投身于洪流的热情油然而生。这就是我们当时年轻人的文化背景。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描写的是一个大腹便便的人到大雁塔上看风景,然后又走下来,融入到人群中。这就是一个普通人作为当代英雄的存在。这背后支撑它的是市民文化。那些吃饱饭,能够去看看风景的普通人,他们离弃了政治的桎梏和集体的绑架,随心所欲地活着,柴米油盐,不追求深刻,也不追求伟大。这就是平民意识,市井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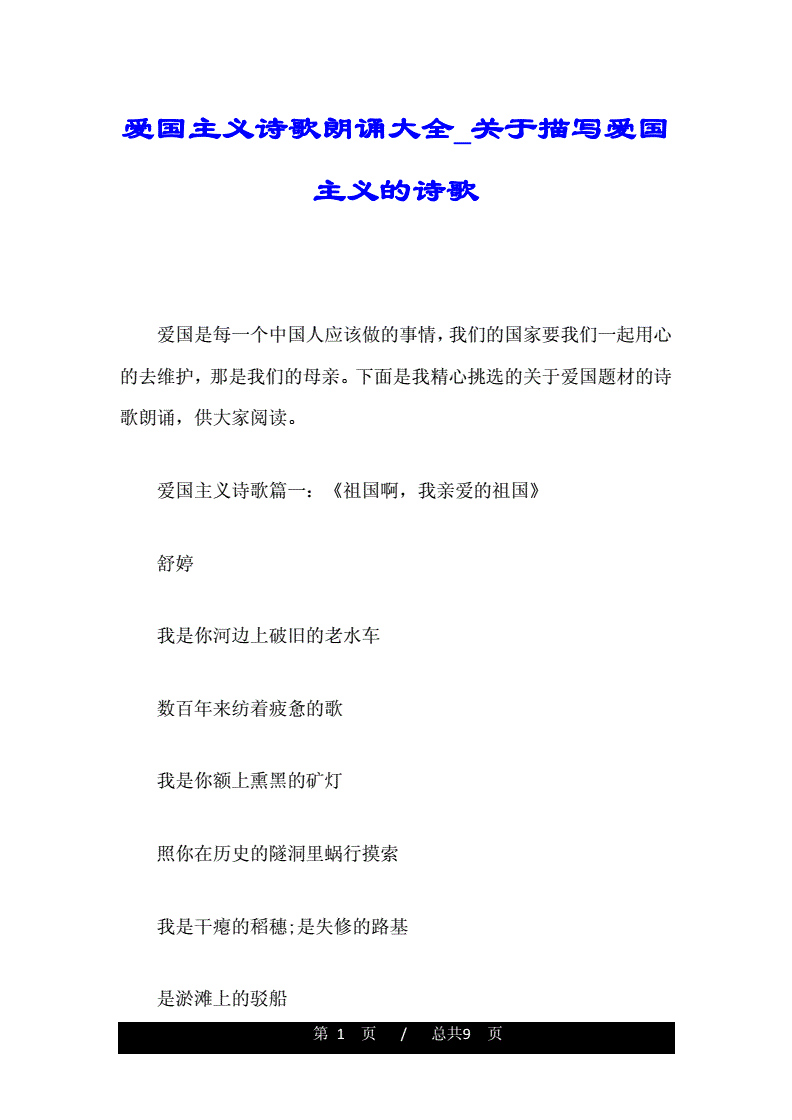
李亚伟的《中文系》嘲讽的是那些食古不化的教授们。他们把具有不羁和山头主义的“黑社会”性质的文化,内化为一种对现代主义一知半解的狂热,包括“Pass”的口号也是一种土匪加革命的本土文化所催生出来的。语言的选择无疑也反映了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的一种状况,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对于前人的文化批判,可能是一种超越、一种扬弃,它们并不是两个阵营,而是一种发展的关系,而为何一定要“Pass”?占山为王的文化和固有的革命语境与语言思维,规定了第三代只有这种思维和语言的使用。
在之后诗歌的热潮中,特别是引发大众热捧的诗歌,像汪国真热、余秀华热背后支撑的文化和社会心理,都是与当时的社会病理——由文化和制度执行的后果——有关;至于其他各种现象,包括梨花体、乌青体、羊羔体等,那是大众传播和社会心理的反感发酵后的催生物。汪国真热是因为八十年代末理想主义遭受挫折后,需要鸡汤疗伤的心灵抚慰物;余秀华诗歌所呈现的是一个农妇在被社会、生活挤压时无法正面反抗,而采取的解构、自贱方式来缓解压力的勇敢者形象,它对应了当代人人都是弱者,被挤压、无法正面反抗、无言的处境,以及由此产生、衍生的解构和自贱的生活方式、心理应急机制等等生存现实和文化心理。
除了这些在写作潮流和大众中产生重大影响的诗人之外,还有无数的在个体觉醒之后,却把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那个普通人的角色或者某种无人之境的文化当成写作的最终皈依,一点市民式小情感、一杯知识分子的下午咖啡、一阵打工者的愤怒、一朵孤芳自赏的鲜花、一座贫困而安静的乡村或者一座破落而想回到儒家孝道的小镇、一片天人合一而人已经死了的自然、一个因愤怒和绝望而自虐自残的人、一个鄙视一切否定一切的人……这些种种的生活和情怀充斥着第三代诗歌运动以来的诗歌写作。他们回避着制约他们思想和生活的社会,而又在各自的小天地里五彩缤纷、自我喝彩;他们不敢,也无力提供更有张力的诗性以及更深邃的诗意。这个时代已看不到伟大的心灵,人人——包括诗人——只能也只敢承认是那个属于日常或者一点“文化”浸润的角色,而对于社会事务、人类事务以及文化的重大建构的角色,却被彻底、毫无意识地在自我的生命中被抽离了;他们——包括诗人们——羞于谈论伟大的心灵、伟大的生命可能;担当让位于凡俗,建构让位于自贱,反抗让位于消解,想象让位于实际。
这种写作成果,如果放在整个世界的诗歌格局里看,现有诗歌的羸弱、匮乏和扭曲就一清二楚了。这些写作的人可能已经是我们时代、我们社会的最勇敢者了,也许也是最有影响的抚慰者和疗伤者,但对于诗歌要建构的世界,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到的诗歌世界——那个有尊严的、宽阔的、充满勇气的、充满爱的、不屈不挠的、葆有力量和存在感的诗性世界——在我们当代的诗歌写作史中,还未出现;更不要说那个具有人类未来意义的、在文化上具有重新创造文明的、指向生命和文化最高可能的诗意世界,还依然被彻底遗忘。我们的个体意识已经觉醒,但才醒来一小半。生命的觉醒是能达到丰盈的程度——即超越匮乏、软弱,超越对周遭处境的盲视,超越某种点到为止的盲目乐观;生命的觉醒是一个心灵能够在方寸之间感知万事万物,能够体验外部世界的轻微悸动儒家佛家道家高语境文化,并且能富有尊严地行动和表达。然而从第三代诗歌运动以来的诗歌写作,我们看到的具有这种表达力和行动力的诗歌和诗人,少之又少;如果有那么三两个,也处在公众和主流意识的遮蔽状态。我们可能无须抱怨公众,因为公众的意识、趣味和认知是被主流意识所塑造、规训和培育出来的,纵使有所抱怨,也是在主流意识的笼罩之下。我们知道,人是被塑造出来的,“我”可以不是现在的我,而是另一个“我”。此时这个“我”,是被他生活的环境、种族,被社会的意识形态,被教育、家庭、周围的人际关系,以及他阅读的书籍所塑造的。很少人能逃逸他的时代馈赠或者说影响给他的文化,纵使他觉醒了,在匮乏的环境下,也没有多少资源能给予他滋养,能提供多少精神资源来给予他进行自我的建构和超越。还有一个非常尴尬并且难以言说的状况,就是摆脱原生社会对个人造成的局限——譬如说你的原生家庭带给你的创伤,你在心理上修复了,或者伤害已经在你成长过程中成功地转移了,你在其他方面找到了代偿性的满足。虽然理性上你知道是个问题,但在心理上你已经不再对此耿耿于怀,这个“病”就这样潜藏在你的生命里。在我们的文化中,在诗人的写作中,这种状况非常普遍,就像肤浅、自贱、恐惧、逃避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且振振有词地强调只能这样——多么可笑的辩证法!
我们时代的诗人正深陷在这样的逻辑里!又有几个人能够超越呢?造成这种状况的无疑出在文化和怯懦、犹疑的文化性格里。而且文化和性格又互为表里,互为催生,在一个巨大的历史、社会的空间里循环反复、生生不已。更为严重的是,对于那些我们自身所涌现的具有活力的思想、心灵和那些带来希望的个体,一味地用冷漠、隔绝、抑制和剔除来对待。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为社会思想的发展打开了空间。这也使潜藏在民间的市民文化、“阿飞文化”、“袍哥文化”,以及古老的东方文化,重新获得了存在的可能,为复活“人”和“个人”注入了本土文化的活力。虽然这些本土文化庸俗、乡土、底层化而有腐朽的气息,但在那个时候,它们与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相比,依然那么生机勃勃,那么富有“先锋”的意义。它们使中国文学、中国诗歌回到了“人”和“个人”的本质上。九十年代之后,消费性的时尚文化继续加入文化的大合唱,多元而又互相冲突、互相压制,甚至互相威胁的局面,使诗歌在不越过制度底线的范围内,得到某种在日常和消费层面的言说自由,和在题材内容上的花样翻新。当然,由于无法触动生存真相实质和文化资源的被选择性使用,这种有限的自由也导致了第三代诗歌运动以来的诗歌写作内在精神的匮乏。从广泛的层面来说,西方的现代个人主义是由古希腊的民主文化、基督教文化、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人本主义、科学和理性文化所充实的,在他们的性格中,还有由基督教培育的对真理追求的不妥协精神。从文化和性格上,造就了西方当代诗歌强烈的批判性和诗歌世界的自我建构的能力。
我们知道儒家佛家道家高语境文化,文化和社会性格两者之间互为表里、互相催动。除了固有的文化的作用,民族性格就是文化作用的结果,反过来也对文化的发展和培育起着抑制或催化的作用。这是由于我们民族在终极追求(真理性事物)失落之后迷茫的结果;我们没有一个类似宗教的信仰,能在现代内化为对真理追求的精神支撑,并且凝聚成一股知识分子的力量。在我们的传统儒家文化中,“孝悌”是文人士大夫这些入世的人的最高归宿,“仁”只是“孝悌”的内涵,“仁”服从于“孝悌”。有一部电影《九门提督》,讲的是一个武将忠于君王忠于父亲的故事:当父亲代表君权和父权要取他性命时,他不知有什么价值可以去追寻,纵使他武功高强,可以战胜他的父亲,但他还是愿意把命还给父亲,让私欲膨胀的父亲杀死自己。由于佛家和道家都是出世文化,它对入世的儒无从起作用;它们也没内化为一种值得奋不顾身去追求的真理。因此,入世的儒家只能殉道“孝悌”——君王和父亲。在历史上,明臣方孝孺纵使被株连十族,也要守卫所谓皇家的正统,而在同一时期,布鲁诺却为“日心说”、对上帝的怀疑等等外在和内在的真理而被烧死。虽然都死得壮烈,但他们的追求方向不同,也让我们看到最终文化的去向不同。“孝悌”文化在经过现代的转换之后,就逐步演变成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了。在古代漫长的历史中,国家是统治者的私有财产,臣民服从的是皇帝、王室或者宗教。虽然族裔认同自古有之,但到十七世纪初,民族国家的现代概念才形成。在我们的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后,人的精神空间依然被压缩在某种单一的意识维度上,这就造成知识分子精神的匮乏、扭曲和迷茫。真理的隐匿,更高的价值缺失,纵然最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由于这种真理性追求在生命中的位置的弱化、隐匿,以至于在国家和民族遭受内部的苦难时,也会处于犹疑和失语的状态。
在内在精神匮乏的状态下,犬儒主义、逃避和移情便成为唯一的出路和臆想中安全的避难所。面对着第三代诗歌运动以来的诗歌写作,面对着我们当下的文化资源、原生社会所塑造的人格心理,建构具有人类意义的诗性世界和诗意世界,无疑成为当代诗歌写作的最高追求。而个人觉醒作为当代诗歌写作的重要成就和写作方向,我们如何守护、如何充实其文化内涵,也就成为诗人在写作和自我建设方面无法忽视的内容。
(《文学自由谈》,2019年第1期)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