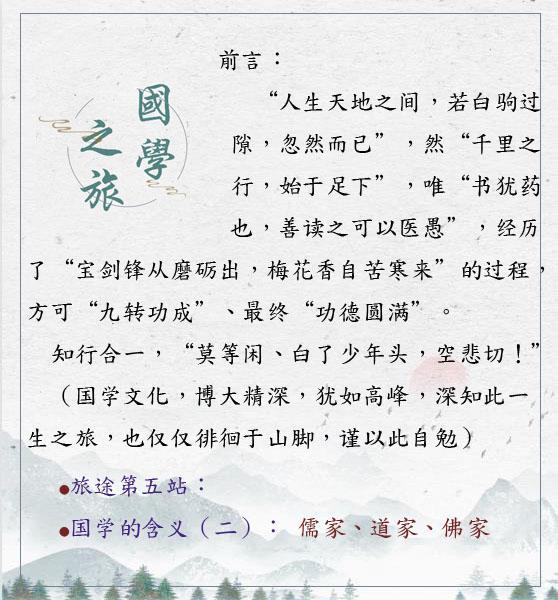内圣外王的内涵便呈现相对多样性[1]

“内圣外王”初见于《庄子•天下篇》,后被援道入儒,经过历代儒者的诠释与耕犁,逐步奠立成儒家政治哲学的中心信念。作为一个已经获得了“主体性生命”的核心观念,在中国儒学展开的巨幅卷轴之中,“内圣外王”俨然成了一个聚蓄感人力量的场域,向历代哲人发出殷殷的召唤,故此围绕它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得出了丰硕的成果,也产生了众多新说岐见。诚如张立文先生所言,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换,人们的价值取向、伦理道德、心理结构、审美情趣亦随之发生变换,内圣外王的内涵便呈现出相对多样性[1]。对相对多样的各种概念内涵进行梳理,不难发现历代哲人的诠释大体存在三个不同维度:一为道德要求与政治效果的维度,即强调为政主体在为政过程中的道德自律,要求他们在不断提升德性的同时陪护社会民众的伦理道德,确保达成“至善”的政治效果。二为道德修养与政治地位的维度,即强调为政主体通过培养、提高自我道德的“成己”途径,经由自内而外、由近及远的落实与扩充,自王道极成王位或王权。三是道德本体与政治制度的维度,即经由“德性直贯”转向“外王之学”的“曲通”,自“道德的心”开出“知性主体”进而“坎现”民主与科学,构建民主政治的“新外王”。本文在前贤时彦的研究基础之上,试图厘清内圣外王在三个维度渐次延展的思想脉络,发掘历代儒者围绕道德(内圣)与政治(外王)所进行的理论运思的特点及其正面价值与思维教训,从而为“道德如何进入政治“这一政治哲学议题的现代开展作出尝试性回应。
一
孔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历来被视作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初声。通过孔子与子路的这番对答可以看出,“君子”人格的极成,不仅仅是个体道德的自我完善(“修己以敬”),而是必须贯达在“安人”与“安百姓”的政治实践之中。此中可见,孔子思想中的内圣外王并非断为两橛,相反保持着内外的连贯。
孔子特别强调:“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尤病诸!”表达了对“修己以安百姓”的审慎态度。对此,孔子回答子贡问“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乎”时的一段话可为佐证———“何事于仁三个儒家哲学的关键概念,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仁”与“圣”的分际,表明孔子心驰神往尧舜时代的理想政治的原因,与其说是执政者具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自我牺牲精神或超凡入圣的道德品格,不如说是他们能够遵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施政原则。“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固然体现了为政者崇高的道德境界,也能焕发出强大的道德感召,然而这是尧舜尚且难以做到的。相反,“忠恕之道”并非悬空于现实世界之外的空想,经由此途去“安人”、“安百姓”已属难能可贵。当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圣”这一点同时说明:孔子认为个体德性生命的完满是一个永无止境、不断超拔的过程,为政者要以终身“病诸”般的临深履薄的精神,不断反求诸己,为政施仁。[2](P67)
有必要指出,孔子思想中的道德要求与社会秩序之间存在着某种映射关系。孔子谓“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里的“君子”与“小人”针对社会位置而言,意指治人者必须以“德”“义”规范自己。但是,道德并非孔子对治人者的唯一要求。子贡问政,孔子答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这就表明:让老百姓丰衣足食,拥有强大军事力量使四境安宁,讲究道德取信于民,都是为政者必须关注的内容。在“必不得以而去之”的情况下,先去兵,再去食,但必须存信。这种取舍次第,表明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优位性。但这种优位性是针对治人者而言的,在治于人者那里,孔子提出了不同要求。在卫国时孔子与学生有过一段对话,藉此可以略窥一斑:“子适卫,冉有仆。
![内圣外王的内涵便呈现相对多样性[1]](https://guoxue.pro/uploads/allimg/20240219/1708326197690_1.jpg)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可见,为政者应当在庶之、富之的前提下,再施加道德教化。这就说明,孔子清醒地知道,为政过程中必须老老实实地解决从吃饭穿衣到道德教化的一个个具体问题,体现出孔子对外王事功的重视,以及他对道德教化在为政次序中的理性安排。
孟子的内圣外王建立在性善论与民本论的基础之上。表面上看,由“不忍人之心”向“不忍人之政”的扩充,即是“内圣”极成“外王”的过程。但是,深究起来却并非如此简单。在回答齐宣王询问“齐桓晋文之事”时,孟子对“保民而王”有详尽的论述。
他认为,若想达成“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孟子•梁惠王上》)的外王效果,需要在实施各项政策的过程中扩充自己的“不忍人之心”,并将此心贯注在“制民之产”的经济制度、“薄赋养民”的福利措施,“由养而教”的政治原则之中。正如黄俊杰先生所言:先秦孟学原有“内圣”及“外王”二面。
孟子所关怀之基本问题虽发端于道德自我之建立,但落实于现实的文化世界与政治世界之中。孟子的理想世界包括内外两面———内而根于仁心,外而发为仁政。[3](P334)不可否认,“道德”在孟子思想中有着超乎“利”、“力”的优先地位,但若因此认为孟子的政治领域即是道德领域的延伸,却是曲解了孟子,因为他在肯定“道德”的同时,仍然坚持“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
也就是说,孟子并没有否认“先王之法”和圣人的“规矩准绳”,他强调的是在此基础之上再“继之以不忍人之心”。陈熙远对孟子的这一观点有着精辟的论述。他说:孟子显然意识到了,仁政显然有其不容化约的运作方式,它是善良的“意图”要成就完满的“结果”时,不可或缺的“手段”。因为善因并不能保证善果。就象以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也无法在不使用规矩的情况下,精确地绘出方圆来。因此,手段不仅是不能化约,而且是不容扭曲的[2](P57)。
与孔子相似,孟子也强调为政主体的道德要求。
他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必须指出,“宜在高位”不等于“必在高位”,前者是“应当”,后者是“必然”,因此在孟子的思想中,内圣是外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而且,与孔子相较而言,孟子标举的“内圣”似乎更加容易达致。在其与齐宣王的对答中,宣王多次强调“寡人有疾”,表示由于自身缺陷难以施行仁政的主张。孟子并没有对“好货”、“好色”、“好勇”之“疾”予以严斥,而是强调要“与民同之”。可见,孟子强调的是政治主体必须发动内在的“不忍人之心”这种驱策力,在具体的为政过程中关注社会大众的福祉,尽力谋求“外王”的实现之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不忍人之心”并不等于内圣道德的完满体现,它毋宁是“内圣”与“外王”两个相互涵摄范畴的共同基点。[2](P57)
二
不少论者认为,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系统化集中体现在“入德之门”《大学》当中。“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前五目归之于内圣;后三目归之于外王,条目之间表现出由近及远的条理性、拾级而上的层次性,一条表面看来理论上成熟、操作上融通的内圣外王递进路线于是筑成。
通过对《大学》与孔子、孟子思想的对比,不难发现《大学》对内圣外王所作的理论加工呈现出了两个倾向。第一,提出“修身为先”的观点,与孔子思想比较而言“修身”的内涵被狭隘化。前文已经述及,孔子认为君子之德的达成包含“不可以已”的三个层次,即“敬”、“安人”、“安百姓”,而且“安人”与“安百姓”的政治实践也是成就君子人格的环节。在孔子看来,如果在“修己以敬”这个层面上就停止用功,舍却了“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话,君子品格无法达成,“内圣”就也无法实现。
《大学》将“修身”定位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后,又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定位在“修身”之后,这无疑是对孔子思想的偏离。第二,提出“修身为本”的观点,道德的政治功用被扩大化。既然“修身”是“本”,“齐治平”是“末”,内圣外王一体,内圣就成了外王的充分必要条件,外王可以视作是政治主体内圣之后的自然流淌。这就难免会使内圣得以强化而外王遭致忽略,造成强于内圣而弱于外王的后果。因此,《大学》的作者抱持“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这种论断也就不足为怪了。汤一介先生对《大学》中的这种“内圣外王之道”有着深刻的批判,他说:靠个人的道德学问的提升,求得一个个人的“孔颜乐处”或者可能,但是光靠着个人的道德学问的提高,把一切社会政治问题都寄托在“修身”上,是不可能使社会政治成为合理的客观有效的理想社会政治的[4](P823-824)。此论颇为中肯。
《中庸》在《大学》的基础上再前进了一步,这一小步的前进,使得“内圣外王之道”完全脱出了孔孟儒家的原有轨辙。且看《中庸》的论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这就把“德”与“位”、“德”与“禄”挂起钩来。本来,孔孟的内圣外王是在道德要求与政治效果这一维度中展开,强调的是善治离不开对为政主体的道德要求,内圣外王被界定在“治天下”而非“得天下”的论域;而依据《大学》与《中庸》的立论,“内圣”不仅成为了谋取社会政治地位的依凭,而且还可以作为争夺天下过程中无往不利的“武器”。这种理论倾向,在现实政治中具体化为两个负面表现:其一是将道德作为政治晋升的工具,促成了道德的工具化。在君主专制的政治实践中,以个人道德(如“孝”)为依据获取政治地位的晋升路径自汉开始就已经形成,基于世俗功利目的出现的道德异化现象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其二是内圣受到极大重视,而外王则几乎被忽略,内圣外王沦为“跛脚儿”,最终导致现实政治中出现了“无事袖手谈心性三个儒家哲学的关键概念,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怪象。这种现象得以产生的理论根源,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早已在《中庸》中埋下伏笔。
![内圣外王的内涵便呈现相对多样性[1]](https://guoxue.pro/uploads/allimg/20240219/1708326197690_3.jpg)
总的来说,《大学》“修身为先”与“修身为本”在内圣外王之道中的确立,以及《中庸》将孔孟的“有位应有德”的要求向“有德必有位”的允诺之转化,在理论上已将孔孟思想中关于内圣外王的“内外两层”化约成了“本末一体”,造成了政治生活中的道德绝对化。熊十力先生对此有切中要害的批评,他说:“君子尊其身,而内外交修,格致诚正,内修之目也。齐治平,外修之目也。家国天下,皆吾一身,故齐治平,皆修身之事。小人不知其身之大而无外也,则私其七尺以为身,而内外交修之功,皆所废而弗讲,圣学亡,人道熄矣。”[5](P672)也就是说:如果以“修身”为本体,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为“内圣”功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王”功夫,内圣与外王难免会断为两橛。
三
宋明理学对于内圣外王的诠释大多没有脱出上述两重维度,对此本文不打算过多着墨。迨至儒学的第三期开展,现代新儒家对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进行了新的思想加工,致力于让“内圣”开出“新外王”。总的看来,新儒家不同学者对此有着迥异的运思路向。用黄俊杰先生的话来说:牟宗三是跳过孟子外王学而思考新外王的开出问题。相对而言,徐复观可以说接着孟子外王学来思考这个问题[3](P400)。然而,这一理论工作的展开却有着同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一方面,当时中华民族在欧风美雨的强力涤荡下一败涂地的社会现实,促使着现代新儒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省;另一方面,西方外王的胜利已经或正在显现出对人文精神的不断放逐,即产生了普遍的精神迷失与人文主义的“意义危机”。用牟宗三先生的话来说:“西方名数之学虽昌大(赅摄自然科学),而其见道不真。民族国家虽早日成立,而文化背景不实。所以能维持而有今日之文物者,形下之坚强成就也。……近代精神,乃步步下降,日趋堕落。……然则有坚强之形下成就,而无真实之背景者,虽曰日益飞扬,实则日趋自毁耳。”[6](P4)一方面倾慕西方的“坚强之形下成就”,即民族国家的建立、科学的发展、自由民主的实现这些外王成就,另一方面又要保留儒家的“真实文化”,避免如西方一般陷入“日趋自毁”的困局。面对这样的矛盾纠结,传统文化中的内圣外王资源无疑提供了一个能够在理论上调和这些矛盾的绝妙设计———有了内圣,西方“意义危机”的困境就具有了解套的可能性;有了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又给积贫积弱的中国送来令人振奋的曙光。
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内圣外王成了在儒学第三期开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本文以牟宗三先生为例予以说明。
牟宗三对传统内圣不可能直接开出现代民主政治有着清醒认识,原因在于,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是“理性之架构表现”的成果,而中国文化中较为发达的是“理性之运用表现”,而“理性之架构表现”与“理性之运用表现”二者显然无法直接沟通。为此,他使用“曲通”或“曲转”的概念以求另一种解决,以“良知的自我坎现”作为沟通内圣与新外王的理论门径。在牟先生看来,包含“怵惕恻隐之仁”的心既是道德之心,又是认知之心,当理性的运用表现否定自身,逆转为自己的对立面,就变成了理性之架构表现,转化出知性主体,开出科学与民主,从而实现理想人格(内圣)到理想制度(新外王)的贯通。
李明辉先生说,这种“新外王”由“内圣”的开出,是一种“辩证的历程”,即指道德主体通过转化为“政治主体与知性主体之挺立”,曲折、间接地开出民主与科学[7](P179-245)。
![内圣外王的内涵便呈现相对多样性[1]](https://guoxue.pro/uploads/allimg/20240219/1708326197690_4.jpg)
论述至此,便不难明晰传统内圣外王之道发展到现代新儒家时,便呈现出了一个崭新的维度,即道德本体与政治制度的新维度。牟宗山先生把科学与民主视作是“形下成就”,可以从“良知之心”这个道德本体“坎现”而成。这种理论设计体现了两个方面的意图:一方面体现了对西方民主科学的向往,希望援引西方的刚性政治民主制度为失落的“外王”补偏救弊;另一方面又反映出对西方文化产生问题的担忧,希望用中国传统文化弥补西方文化“意义危机”之失。“他们都希望并强调在保持本土道德哲学的独特品格和文化价值的前提下去消化西方政治思想系统的若干基本因素,藉以实现在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中完成中国社会的政治现代化的目标。”[8](P2)但是,呼唤刚性制度的“新外王”尽管确有新颖之除,就“开出”的理论机制而言,它不过是在自《大学》开始就已经确立的“道德优位”理路上的进一步延伸。
有论者认为,现代新儒家的内圣外王新说,实际上将道德凌驾于其他人类活动之上,将道德视为人类一切事业的主宰,实可谓是“良知的傲慢”。还有论者认为,内圣开出新外王还只是一种可能性,可能不代表必然,儒家内圣外王之学数千年的发展并没有开出科学与民主已是不容辩驳的客观现实。
更深层次来看,西方的民主政治与儒家内圣外王有着完全迥异的文化基础,怎样由内圣开出了新外王,二者又如何契合———这些始终是不得其解的难题。但是现代新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的理论创建有着引人深思的启示:一方面,他们已经开始反思刚性外在制度(民主政治)的必要性。人类既然再也无法将从潘多拉盒子中跑出来的东西重封起来,并且又从未放弃过更温暖、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难道不应该在不断增强自身免疫力、使我们具备更大的力量抗拒它们的同时,再竖起一道防范的篱笆吗?另一方面,中西文化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抑或更具体的说,中国文化的“道德人文精神”与西方的民主政治之间,是否就必然是针尖对麦芒的关系?难道就不可能通过理性的选择,通过取长补短最终让二者相辅相成?
四
以上从三个维度对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进行了粗线条的分梳。以下,再对各个维度的立论旨趣、道德在政治中的安置,以及各个维度所蕴含的政治哲学意义略作分析。
孔孟的内圣外王从道德要求与政治效果的维度立论,关注的焦点汇聚于“德”与“治”的层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孔孟的内圣外王表现出“圣”与“王”分解的倾向,分别代表着伦理与政治的两种状态[9]。内圣与外王之间,不是简单的创生与推展逻辑,其运思的根本着力点是为了达成外王而对为政主体作出德性规定。孟子对“德”“位”关系的论述,将政治权力的转移与道德挂钩,具有政治哲学上的深刻意义:即“一个伦理主体担负了某种道德,他可以外王;然这个伦理主体丧失了这种德性,他就失去了外王资格”[9]。后世儒家正是以这些思想作为理论的武器,对君主专制发起猛烈抨击。从这个角度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孔子孟子那里,道德秩序本身不是终极目的,免予苦难与眼泪才是他们的终极关怀[10]。《大学》与《中庸》对孔孟儒家道德与政治关系的理论加工,使得将内圣和外王糅合在一起讲的倾向得到了加强,将“德”与“位”、“德”与“治”统统纳入道德统御之下,企图把“圣人”造就成“圣王”,而由“圣王”来实现社会政治理想。这样,内圣置于本体地位,外王却屈居其下,不但使得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目的无形之中被弱化,而且“格、致、诚、正”这类主体修为也被抽离现实环境,内圣与外王被生生割裂。
之所以在《大学》与《中庸》中会发生内圣外王之道的理论转向,实可以从外缘影响与内在理路两个方面找到原因。就外缘而言,主要基于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我们知道内圣外王的内涵便呈现相对多样性[1],春秋战国时期是早期宗法制向地域国家制过渡的时期,平等的民主遗风逐渐隐退,最高统治者的专制权力不断加强。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化,实为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从“圣王”到“王圣”演变提供了现实基础。就内在理路而言,内圣外王之道的转向在孔孟“义命分立”思想中埋下了理论“伏笔”。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
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孔子一方面强调应该行“道”,另一方面又认为而“道”之行废取决于“命”这个外在的客观决定因素。“义命分立,即‘是非’与‘成败’分家,‘应该要做’与‘如何成功’分属两个不同范围。后世的儒学一直沿义命分立的路向发展,结果儒学一直强调内圣,也强调‘应该’外王,可是究竟如何外王,即令事功达致成功的客观方法,却不甚了了。”[11](P137-138)现代新儒家的目标,正是要克服传统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制度缺失之弊,将民主政治作为“新外王的第一义”,然而其哲学运思实质上仍然停留在内圣外王“一体化”的思维框架之内,将孔孟的“怵惕恻隐之仁”亦即其“道德的理想主义”放置在形上的层面,在开出民主与科学的目标方面采取的是拿来主义的手法。这就不仅使得“在理论逻辑上无法架起传统思想与现代政治之间的桥梁内圣外王的内涵便呈现相对多样性[1],在现实的层面上,也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存在巨大的鸿沟”。[8](P190)
众所周知,在西方哲学后现代转向的凯歌高唱中,道德被驱逐出了政治的领域,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因此成为了集簇着无数批判之矢的箭垛。令人遗憾的是,排遣了道德的政治似乎并没有让人们变得更温暖、更理智、更亲密、更幸福,政治依然充斥着“说谎与欺诈的骗术”,“掠夺与压榨的一个霸术”[12](P1),而且神圣的道德法庭破产之后,按照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模式组织起来的世界蜕变成了一个无灵性的世界。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现实场景,引起了中西方学者的重视与反思,如何重构政治哲学,找到道德进入政治的通道,成了一个新的课题。在这一背景下思考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至少可以为我们提供这样几点启示:第一,重新定位内圣与外王的关系,在外在制度建立方面,要打破内圣外王一体化思维模式的局囿。
不容否认,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在进入了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导致了忽视对外在刚性制度建构的后果,以及将道德凌驾于政治之上的问题。以牟宗三先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虽然力举发展民主与科学以求现代化,开始重视外在制度的建构,但同样缺乏对与外在制度相配套的思想和文化基础进行考察。实际上,即使我们确认西方的民主政治是现代社会政治的基本发展方向,它不能也不会由“怵惕恻隐之仁”的道德本体衍生。这种思维教训是我们今天必须深以为戒的。当前,随着现代生活世界发日趋强劲的公共转型,理性化、制度化要求越来越迫切,认为“政治问题就如社会问题一样,首先是个道德问题”,并寄希望以道德涵盖人类的一切实践,以道德政治化解决民主政治中“恶”的问题,都是缘木求鱼的做法。根据政治、经济、文化等基础性条件,在小心陪护政治伦理与政治美德的同时,探索、选择、构建并不断完善外在的刚性制度,这些都是打破内圣外王一体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必须认识到政治伦理和政治美德是建构良善政治与良序社会的思想基础和必要资源,因而必须纠正对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作“泛道德主义”理解的错误认识,尽可能地从中吸取有益的思想资源。
上文对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三个维度的分梳说明,对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单纯作“泛道德主义”的理解是片面的。从道德要求与政治效果的维度来看,儒家内圣外王的核心期望不能简单理解为以道德理想转化政治,而是要求在现实政治中倾注道德关切,藉此追求良好的、能够带来或引导大众向善的政治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在今天仍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积极意义。而且即使是民主政治基本完善成熟的西方,在具备强有力的外在刚性制度的前提下,这个维度的意蕴依然具适应性和生命力。因为,在任何时代,对为政主体提出一定标准的道德要求都是必须的,对社会公民进行政治伦理与政治道德的教化都是必要的。从执政者的层面来看,在一个人自己内在教养不严的情况下,也就是“内圣”不足的情况下,如果有一天他身居高位,很可能会以制度的合法性做出祸国殃民的事情。[13]
另一方面,如果普通公民不具备基本的政治美德,制度的规范效用很有可能会因为内在的抗力而抵消,或者说即使发挥效应也是消极的。个中情由,万俊人先生已作论述,他说:公民个体的政治美德和基本道德的修养水平乃是确保制度规范普遍、持续发挥其规范约束效应的主体基础,更是制度规范可能高效运作的必要主体条件。换句话说,仅仅确保制度设计、制度安排和制度操作的正当合理还只是确保制度规范效应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后者的有效供应有赖于公民个体的主体行为动机能量,而这恰恰只能通过培养和提升公民的政治美德及一般道德水平才能产生。[14]
不过,我们还必须看到,肯认儒家内圣外王蕴含的积极意义,并不意味着道德进入政治的过程就是一个通过重建传统文化三个儒家哲学的关键概念,以求对治现代中国问题之药方的运思模式;但同样也绝对不是一个全盘否定传统,无视传统文化资源的悬空设计。我们应该立足时代场景,吸纳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成果,在制度设计和道德陪护方面,都要进行创造性地转化。当今天人们为政治哲学的重构提供各种尝试性的解决方案时,不应当忘记:在人类政治生活中,既要避免德性的僭越,又要避免德性的缺失。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