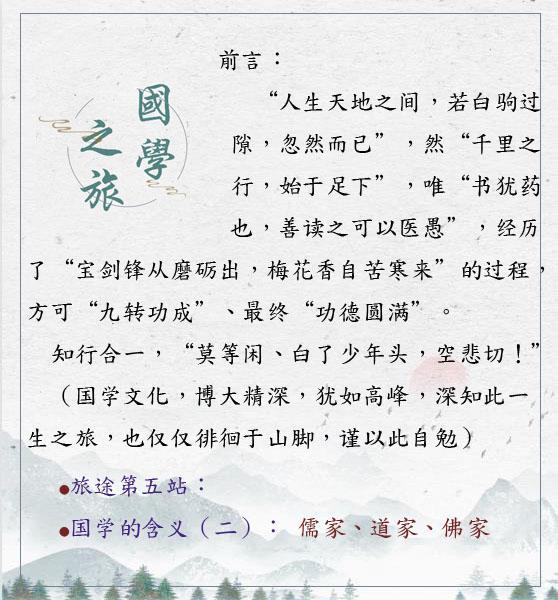宋朝的“杯酒释兵权”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
前言
事实上,不仅北宋之前的五代十国已经出现了由于生存压力的严酷而导致的精英阶层的道义尽失、纲常崩坏的现象,而且魏晋南北朝也曾有过类似的悲剧。然而,与此前不同的是,宋朝的“杯酒释兵权”是一个国策,是一个从上到下的系统性工程,是对整个精英阶层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的制度性安排。在这种背景下,不仅从体制中获利的整个官僚集团反对王安石的改革动议,而且政权的所有者———皇帝本人也不敢或不愿轻易改变规则,因此王安石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改革困局:他建议的制度变迁是一个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但他却并不能像此前的李世民、此后的张居正和雍正一样拥有强制性的执行能力。
宋朝的精英与大众已经受到了商品经济利己主义之风的影响宋朝的“杯酒释兵权”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甚至感受到了商品经济带来的短期利益。因此不仅从统治者到官僚阶层都对集体主义利他精神不感兴趣,整个社会精英群体普遍缺乏传统儒学不断强调的正统道义及其推崇的利他心,而且社会的下层也在精致利己的精英们的煽动下盲目跟风堕落,以至于社会大众也在利己精英的鼓动下反对有利于公共经济效率改进但却会影响短期个人利益的改革措施,从而使整个社会主流文化陷入空前的危机,使具有外部性的利他主义思想与公共经济理念陷入绝境,为后来的内忧外患埋下了伏笔。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王安石敏锐地意识到国家治理成功的关键正是公共经济需要的集体主义道德,而对公共经济执行者进行的教育培养是集体主义精神培育的基础。在《商鞅》诗中,王安石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万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他深知,北宋的社会危机主要是公共经济的危机或财政体制的危机,而造成问题的关键则是理想教育出了问题,是社会精英的自私利己削弱了以公共经济为对象的国家治理能力。面对北宋“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的窘境,王安石敏锐地观察到财政困局与社会危机的根源所在,认识到北宋原有的财政体制无法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
他一方面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公共经济供求对应新主张,力图通过调节国家的财政收支重新建立起能为北宋提供充足有效的公共产品的财政体制;另一方面,他力图从精英教育入手,改变官僚阶层的道德思想与文化理念,重塑以利他主义精神为内核的儒家学说的正统价值观。他主张,作为一个公共产品的提供单位,国家内部应实现有序的分工与合作,并由政府主导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政府不仅应协调好政府、富人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且要同时满足上层精英的发展型公共产品和下层弱势群体生存型公共产品的需求。为此,王安石提出了一系列的变法主张。

(一)采取措施“节流”
王安石变法首先主张裁兵,变法实行的“裁兵法”一方面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另一方面对现役士兵进行测试,经过测试,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儒家思想的缺陷,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同时,对名额不足的军营加以合并,对老弱不堪的兵士予以淘汰。在对军队进行全面的整顿后,全国厢禁军总额为79万多人,比宋英宗治平年间兵额减少了36万多人,比宋仁宗庆历年间减少了45万多人。此外,变法期间对州县等行政机构也进行了合并和裁剪,同样缩减了大量的公职人员和俸禄开支。
(二)重新分配社会财富
王安石变法的另一主张是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一方面裁减官绅豪强大地主和豪商富贾们所享已久的特权,限制他们非法积累财富的“自由”;另一方面,通过在全国推行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青苗法、免役法等政策,将财政支出用于有利于“减贫济贫”小微民营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造福百姓生计、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同样儒家思想的缺陷,“青苗法”意在限制较高的贷款对农民的剥削,“募役法(又称免役法)”则力图把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劳动时间,促进生产发展。总之,以上变法措施存在一个共性,即将纳税义务与财富拥有量挂钩,以便让富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救济帮助更多的弱势或劳动群体。
王安石的这种“富国乃富天下百姓”的思想,在他的《与司马判书》以及《答司马谏议书》中都有详尽的阐述。他写道:“尝以谓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资其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王安石救济弱势群体的理财思想反映了他“回向三代”的政治趋向儒家思想的缺陷,反映了他希望统治者与社会精英“法先王之政”、回归正义道统的治国理政理念与公共经济思想。

(三)加强官僚队伍建设,回归天命伦理正途
当然,王安石深知,北宋的社会危机关键在官僚队伍,根源在思想认识。因此,变法的关键是国家官僚队伍的建设,而变法的基础则是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培训与教育。王安石一方面痛心于当时的官僚阶层社会精英逃避公共产品提供之责的局面,另一方面也对变法的实施将会遭遇的重重阻碍有所预料,特别是对上层有意推行的腐蚀精英阶层的“杯酒释兵权”与“给赐过优”经济赎买政策的余毒与影响颇有思想准备。因此宋朝的“杯酒释兵权”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在嘉祐三年的《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一文中,王安石提出了一套系统全面地培养公职人员集体主义道德与正义道统利他心的办法,努力用教育来奠定变法的思想基础与组织基础。在具体的措施上,王安石将其概括为“教之、取之、任之、养之”。
首先,他指出,当时的学校弊病甚多。学校教育的内容,空疏腐败。“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己”。其结果是,学生连年累月地死读硬记,把精力都消耗尽了,也没有学到有益于治国平天下的真才实学。所以,一旦“使之为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
为了培养和选拔出充足的可为国家所用的具有集体主义精神与利他主义道德的人才,王安石倡导“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博置教道之官而严其选”,对于教育的内容,“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法在于学”,力图从思想道德上教育引导,“使天下人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学校的课程设置上,以“尚实用”为原则,他所提倡的教育内容实质是“治天下国家之道”,具体来说则包括德性的养成及处理具体政务能力的培养。其目的显然是培养政治精英或国家治理者,即所谓的“公、卿、大夫、百执事”。

其次,在人才的选取上,王安石建议,在科举中,废罢明经试科,增加进土名额。进士考试,取消诗赋、贴经和墨义,改为经义和策论。在人才的任用上,基于“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的认识,王安石再次强调了德才兼备的传统观点,认为应以个人德才的高低为依据在社会有序分工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公共经济治理功能,任用那些能“在其位而谋其政”的人。
此外,他还认为,在人才的任用上,应该“久任其职”和“得行其意”,确保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甄别人才的德行。因为任职时间较长,贤能的人才可以做出成绩来,不肖的人才可以得到暴露,从而有利于官僚队伍的责任意识的养成。当然,选拔、任用治国人才之后,还需配套的制度构建来保障统治精英切实有效地履行公共产品的提供职责。为此,他积极推行高薪养廉的制度以遏制腐败。王安石认为,“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是大多数人的常态。
也就是说,在商品经济的背景下,除个别利他精英者外,大多数官僚的集体主义道德极易受到个人主义意识的侵蚀,如果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极易陷入腐败的陷阱。因此,俸禄的制定,应保证“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甚至“使其足以养廉耻”或“推其禄以及其子孙”。在王安石看来,养廉之道的核心是确保精英阶层的物质财富基础,虽然“仓廪实、衣食足”不能保证必然“知荣辱、知礼义”,但“足于财”显然是“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的前提条件。

总之,在王安石的官僚体系构建方案中,“教之、取之、任之、养之”的政策措施,都是以德行的培养即公职人员的集体主义精神与利他主义道德的塑造为目的的。然而,他也深知,仅仅强调道德教育而没有法律强制性,肯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针对“婚丧、奉养、服食、器用之物,皆无制度以为之节,而天下以奢为荣,以俭为耻”的乱象,他又提出“约之以礼矣,不循礼则待之以流、杀之法”的政策建议,即主张利用礼法相结合的手段来以刑辅德。正因此,学术界才长期存有对王安石变法思想是“推儒”抑或“崇法”性质的争论。
实际上,因致力于实现国家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目标,王安石的变法手段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兼收并蓄的。正如邓广铭先生在其《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书中所言,作为政治改革家的王安石,实际上是一个援法入儒的人。的确,王安石对统治阶层德行的强调虽是继承了以维持内部秩序为目的的儒家文化,但为了弥补儒家文化在约束力方面的不足,王安石的许多思想主张都是儒法并举的。如“加小罪以大刑”及“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在经过他的引申阐发之后,几乎与先秦的法家们所主张、所实行过的一些论点和措施完全相同。
结语
此外,他主持修订重释的《诗》《书》《周礼》等都是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他强调,对百姓有利的制度措施才是真正的先王之道。王安石清楚地认识到儒法只是手段,不应因“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他自己在《王霸》一文中也谈道:“仁义礼信,天下之达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因此,两者结合既是减少改革阻力的“托古改制”,同时也是为了通过礼乐刑法的使用保证国家治理结构有序运行的创新尝试。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