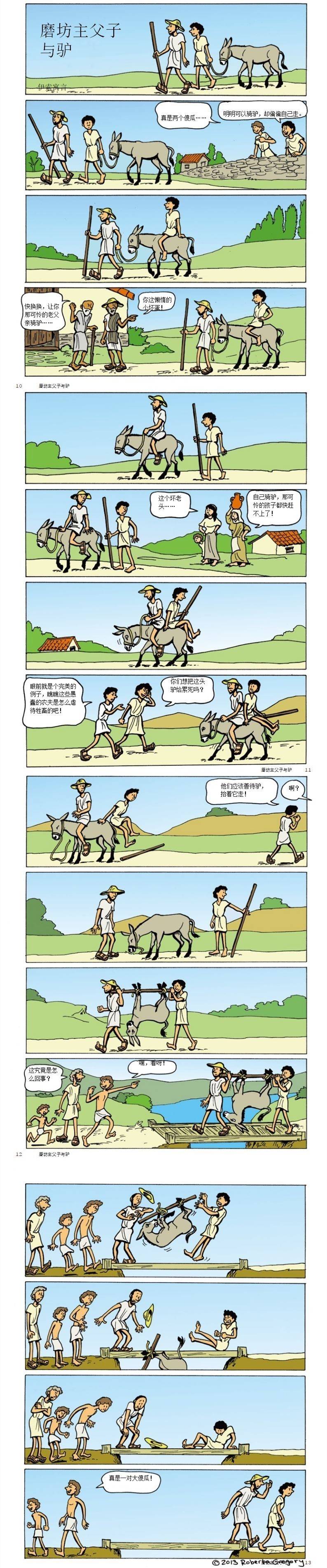自然法思想的实质和实质的区别
摘 要:中华法系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儒家以天理为其评价社会规范的最高准则,并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融入其中,认为“礼治”是社会治理的最佳手段。这种“天理”观是自然法思想的表现。礼是自然法的现实化,而贯穿在这种社会治理思想中的是一种朴素的“民本主义”。虽然这种自然法思想的发展不能和西欧自然法思想的发展相提并论,但确实起到了抑制“人治”恣意的作用。
关键词:自然法;天理;民本;礼治;法治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一、自然法思想的实质:法外之法
“自然法”通常是指与实在法相对的,更高层次的法律,一般而言后者应该服从前者,并因此而获得合法性基础。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 最早论及自然法问题的是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认为法律有自然法和人定法之分。自然法是反映自然存在秩序的法律, 如主仆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自然存在的秩序”, 而自然法就是这种自然秩序的反映, 其内容是普遍适用、永恒不变的;而人定法是由城邦制定的法律,其内容是经常变化的, 自然法高于人定法, 是人定法制定的依据。第一次系统地阐述自然法学说的, 当推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西塞罗的自然法学说把法律与人的理性紧密地联系起来,认为法律的本质应该从人的本性中去探求, 而人的本性就是理性。他指出:人是众多生命当中惟一获得理性和思维的。从人的本性中探求法律的本质,也就是从理性中探求法律的本质。那么, 人的这种本质或者理性来源于何处呢? 西塞罗认为源出于自然。在西塞罗看来,人有着共同的本性,如人总是以愉快和痛苦为标准, 检验每件事是称心或不称心;总是回避死亡、痛苦而寻求乐趣等。人的这种本性是来源于自然的。而人的本性就是理性, 理性是与法律相通的, 理性又源出于自然, 因而法律与自然是相通的, 这种与自然相通的法律就是自然法;所以, 在西方法学传统中, 自然法就是指反映自然之秩序、体现人类之理性, 普遍适用于人类一切行为的永恒法则[1]。
诚然,“自然法”一词发轫于西欧,为中国所本无,但类似思想,我国古代也有论及。如《易传•序卦》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 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即是说人的“礼义”皆出于自然,是“天地万物”等自然秩序的反映, 既然“天经地义”是至明之理,“礼”也就获得了同样的正当性。当然从逻辑上讲,这一推论实际上是在偷换概念。老子认为,天地万物及人类均受自然律的支配, 生息于无始无极的宇宙之中。老子称自然规律为“道”, 并认为: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2]。至于儒家,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于道为最高”[3],向来提倡礼治,认为人伦秩序是一切秩序的基础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大自然思想,对律法始终抱有一种警惕的审慎态度,如孔子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4]
二、儒家自然法思想的渊源:天理
冯友兰先生将“天”的意义归为5种:第一是“物质之天”,就是日常生活所看到的苍天,与大地相对;第二是“主宰之天”或“意志之天”,即宗教所说的人格化的有意志的至上神;第三是“命运之天”,也就是民间所谓的运气;第四是“自然之天”,亦即作为自然界整体意义上的天;第五是“义理之天”或“道德之天”,强调天是人类道德生活的终极价值,人类道德生活的超越根据,道德律法都可以溯源于此[5]。在农业社会,自然条件关系着收成与民生,天与地成为人最大的依赖。出于一种不安全感,当时的人很容易相信“上天”神话的同时将其人格化,使之成为消灾去祸的祈祷对象。元代杂剧《窦娥冤》中的名句“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从反面的绝望角度反映了天在民间所占的重要心理地位。至于平时的乡间俚怨,妇女一边抱头痛哭,一边不忘仰天大呼:“天啊!”“没有天理啊?”之情形亦可佐证“天”这一含义在现实社会仍然有其批判意义和价值依托。
考查“天”在中国政治法律制度上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夏、商、周的“天命”、“天罚”观念。“有夏服于命”,“有殷受天命”,这样的记载都印证了夏、商统治者在“天”上寻找合法性的基础。其逻辑为:天生万民,因此万民自然应当由天来统治;天又将这种统治权授予给当朝统治者以委托他们代理上天管理臣民。至于为什么上天偏偏将这种权力授予给这部分人,则是通过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6]之类的神话传说来化解其逻辑上的虚弱。为了表示对“天”、“上帝”的敬重,商族人几乎每旬必祀。这也是后来“礼”发展的渊源。到了西周则发展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思想。
对“天”这一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儒家思想家们正是从冯友兰所说的第5种意义上,即“义理之天”或“道德之天”的意义上来吸收的。由于“天”这一意象为在上的士阶层和在下的庶民所普遍接受,儒家思想家也总是在其中来论证自己道德理想和救世情怀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所以,与西方自然法不同,儒家认为自然法不是寰宇之内的最高实体,而是“天”的意志的展现,与“自然法”相对应的概念则为“天理”。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7]在这里,“天”不是被取消了话语权,也不是非人格化了,而是实现了圣人式的无为而治,所以大言希声。同时《论语》中又记载了夫子“闻风雷必变”,说明了至圣先师对这种神秘力量所怀有的敬畏之情,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8]儒家将天命理解为宇宙的生命力,却拒绝将它变成佛陀或者耶稣式的神。同时儒家也把道德行为的原动力挂靠在到宇宙生命本体上,这不仅为人类的道德生活找到了超越于尘世的依据,而且也将人类道德行为的意义上升到了宇宙的境界。“从宇宙的大生命的高度,来看待人在尘世间的道德行为,从而使人的道德行为具有了超道德的价值。”[9]在这种意义下的天命,成为了演化自然法的依据。
“天”作为自然法的渊源确实找不到任何依据,但是环顾世界,斯巴达的来库古立法以阿波罗神为依据,《可兰经》被宣称为是天使哲布勒伊所受,《摩西十戒》则是以神谕为其基础。究其缘由,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在程度幼稚的社会,固不能无所托以定民志,而况夫既持‘道本在天’之说,则一切制作,自不得不称天而行。”[10]可见以神秘力量增强立法的权威是民智未开时期的普遍现象,这一方面体现了执政者对于立法的严肃态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巧妙地使法律的权威深入人心以获得自觉遵从。此外从技术上说,儒家注重实用理性,不看重逻辑推理,对“巧言令色者”极为反感,以“天”为起点,一切逻辑上难以解释的东西在此都可以得到圆满答复,使得其整个伦理思想体系浑然一体。
三、儒家自然法思想的凝炼:礼制
天道为儒家观察问题提供了更高标准,孔子甚至说“朝闻道,夕死可矣。”[11]问题是既然天道只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要化作尘世间朝朝暮暮的洒扫应对则必须对自然法加以形而下的把握,使之成为有迹可循的“形器”。那么儒家是通过怎样的手段来宣称天道的存在并进而要求立法者予以尊重乃至服从的呢?如果这种“义理”来自儒家自身的学说,肯定难以得到公认。事实上,从儒家的第一位代表人物孔子开始,就宣称自己的思想“立于礼”,他还语重心长地教导学生“一日克己复礼而天下归仁焉。”关于礼,古书有许多定义,如《礼运》:“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礼记•乐记》:“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可见在经典古籍中,“礼”既是自然秩序又是社会秩序,并且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这种客观的存在说白了就是习惯和传统。古希腊人则不同,他们历来重视探索自然,也重视探索自己,通过理解一方来更深入地理解另一方;因此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是分开的,他们的自然法紧扣着人的理性,这种思想也深深影响到了后来的征服者。
总之自然法思想的实质和实质的区别,《礼》在儒家手中成为了沟通天道和现实秩序的可靠桥梁。这种思维方式也成了推动中华法系发展的一种内在动力;因此“礼法之争”从春秋战国颁布成文法开始到清末法制变革,一直是我国古代法制发展历程中一条或明或隐的线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了解“儒法之争”就不可能懂得中华法系的精髓。那么,“礼”何以能代替抽象玄虚的天道承担起规律社会生活的任务呢?
(一)“礼”的起源
首先,让我们简单考察一下“礼”的起源。穗积陈重认为:“礼也者,行为之有行的规范,而道德表彰于外者也。当社会发展之初期,民智未昧,不能依于抽象的原则以规制其行为。故取日用行习之最适应于共同生活者,为设具体的仪容,使遵据之。”[10]104早在夏、商、周时期礼就广泛存在,直至西周初年,在周公姬旦主持下,以周族原有的习惯法为基础,结合现实需要,制定了一套完备的礼仪制度,后称“周公制礼”。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及社会的变迁,出现了“礼崩乐坏”的现象,社会原有的秩序被打乱,诸侯相互征战。为了重建和谐平安的社会,仁人志士纷纷向当权者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此即史书谓之“礼失而求诸野”。儒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试图收集整理散失的礼以作为社会治理的准据,而这或许也正是孔夫子“述而不作”的重要原因。“法”在古代实质上指的就是刑罚,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五刑”的核心体系。儒家在感情上是抵触“法”来主导社会治理的。两千多年前,汉朝大将军霍光召集并主持了盐铁会议”,“文学”与“大夫”分别代表儒法两家的政治观点展开了极为激烈的辩论。文学批评法家严格执法的观念“深之可以死,轻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夫不通大道而小辩,斯足以害其身而已。”[12]但理智上他们也明白“徒善不足以为政”,[14]所以“刑”只是法的补充。“礼之所去,刑之所取”,“明刑弼教”,“德主刑辅”这些历史上的法制指导原则都是融礼入法的思想结晶。
(二)礼的功能
礼治与法治是现代学者们对古法比较研究时的一根主线,而且往往认为不是法治的就是人治,所以礼治就是人治。这种非白即黑的对立思维并不符合现实,更不利于我们对古法作深入的研究。人治与法治的根本区别应该是看在个人意志与法律规定发生冲突的关键时刻到底是人说了算还是法定的算。礼治显然是反对个人意志可以凌驾于传统之上的,所以孟子才会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13]
前已说明,“礼”实际上就是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将社会经验与个人习惯两相扣合,使天道自然地转为人道,不仅是一言一行,乃至于一闪念的“违道”之志也要受到约束。汉代“春秋决狱”中所谓的“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14]即是这个意思。礼与法最大的不同就是礼是靠着传统来推行,而法要靠国家力量来实现[12]。传统中有清晰可见的部分,也有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部分,一个人又怎样才能知礼而后立于礼的呢?礼所植根的土壤是乡土社会,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重在人伦的维系上。所有的“礼”莫不建立在“五伦”的格局上,“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15]每个人在出生之前已有前人为他准备好了应付一切社会关系的经验,只待他主动的参悟和服膺了。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16]这里的“自得”绝非 “自由”之谓,而是“自德”的意思,即要求君子要在周围的人际关系上下功夫,认真钻研其中奥妙,在日复一日,年过一年的重复过日子中寻找自己的正确位置,最后才能领悟到“左右逢源”的乐趣。如此这般的学问又岂是一般人所能融会贯通,更不消说将这人际上的运用之妙化为心领神会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了。孔圣人直言70岁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13],故即便是圣人这份“自得”也是来之不易。不过这倒丝毫不减礼规范社会秩序的功用,反而能让礼自成一门学问,让莘莘学子负笈一生以求“知书达礼”。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礼治要成为可能,必须是其中的经验能够实实在在地应验,在真人实事上见出分晓。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恰好满足了这一要求。在祖祖辈辈都生于斯长于斯的田地上,“种田的老农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的变更。”[17]过去应验的法子过了几百年仍然可以用,因为社会环境和几百年前比起来还是一样的。传统造就了礼治,礼治又在朝夕之间的洒扫应对中反复排练着传统,最终不是礼治理了社会,而是社会治理了礼。当然,在社会动荡之时礼治秩序就会遭遇危机,这时候就需要有高度威慑力的刑来维持秩序。这就是整个古代社会都贯彻着“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的刑事政策的原因。中国古代虽是农业社会,但从来不乏一些大城市,这些都市人口比较流动、聚集着巨家大户,仅仅依礼而治难以维系,于是有明法的必要。另一方面,人口不断增多,淳朴的民风单凭社会舆论和习惯维系不免单薄,而有借助政府强制力保障的必要。这样就有了中华法系发展过程中最天才的创造,即融礼入法。虽然局部可能不断地产生一些变动因素,但就整个社会而言,维持静态均衡是一种绝对趋势,甚而有削平突出部分的必要。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从西汉王莽到王安石再到清末的康梁没有一次变法得以成功的根源。
(三)结论
总之,“礼”不仅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加诸人身,更是一种人格修养而需“学而时习之”,所谓“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8]依照“礼”的各种规定行事,借此完善人格,人人皆能有完美的人格,也就实现了“无讼”,所以真正的太平盛世是不应该尚法的。
四、儒家自然法思想的制度展开:民本和王政
(一)民本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处处渗透着深刻的人文主义,而“民本”自然成为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奋斗目标。马棚着火了孔子问人不问马,孟子则一见梁惠王就大谈“仁政”而绝口言利,就连主张“性恶论”的荀子也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19]。尤其是孟子,倡导民本思想最力,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思想,甚至极为大胆地提出天子如果暴虐就会沦为“独夫”、“民贼”,人民就可以把他废弃或诛杀。但这里似乎有一个悖论,儒家既然这么看重“人”而主张“以民为本”,为什么没有进而在政治上推演出民主观念呢?这是因为民主观念是受自由主义思想哺育而在政治领域结出的硕果,儒家仅有人道主义的心灵关怀而无个人自由的意识,自然不可能认为国家大事可以由君子小人混杂、上下长幼不分的人民大众来投票决定。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孟子不遗余力地痛骂杨朱“为我”和墨子“兼爱”这些自由主义思想是无父无君,与禽兽无异,宋明理学更是宣扬要“存天理、灭人欲”。孟子思想上的“专制”味道其实在孔子提倡“礼治”之时就已经种下了“业缘”,因为礼发挥功用的社会基础必须是封闭而静态的社会关系,若听任个人自由意识勃兴,必将摧毁这一基础,进而“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儒家既然将“礼”视为当然,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警惕自由主义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大自然思想,进而无法延伸出民主思想的支流。西方自然法以理性为出发点,注重个人意志的自由挥洒,经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的洗礼诞下了社会契约论的果实,进而提倡民主,主张国家主权在民。如此对比看来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虽同是一种关怀,却本于截然不同的民情风俗而生出截然不同的典章制度。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精神的崇高和可贵!如果我们将视角深入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去,尤其与法家的治国思想作一番对比,将更能深刻体会此点。儒家和法家的共同点是都想以自己的方式来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他们的不同点在于这种秩序究竟是“礼治”的还是“法治”。春秋战国之前的法律原则是“礼不下庶人自然法思想的实质和实质的区别,刑不上大夫”。儒法两家对社会的重新治理的计划也是由此出发。“儒家则欲以筹昔专适用于贵族之法律(即礼)扩其范围,使适用于一般之平民,法家则欲以筹昔专适用于平民之法律(即刑与法)使适用于一般贵族。此实“礼治”“法治”之最大争点,而中国进化史上一大关键也。”[10]109-110两种治理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礼治”的实现借助的是社会的力量,而“法治”的实现依靠的是国家的暴力。前者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整个历史都是维持这种规范的力量,而且实施起来也比较富有弹性。对“礼”的制定权也被限制在传统的力量中,反对统治者滥设规定。这恰恰是对“人治”的一种约束;因此,可以认为“礼”的广泛适用是有限地扩大了庶民的平等权,并且以“仁义”的价值指向凸显的人的尊严。这些都昭示着儒家自然法思想“民本主义”的可贵。
(二)王政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20],“礼法合一”后既要有人做出表率,引导民众“居仁由义”,也要有人来制定法令、执行刑罚,这两种需要造就了一种极大的治理权。从逻辑上说这种权力的执掌者应该是道德上最高尚的圣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伦理关系上居于金字塔的顶点,也才配为民做主。然而儒家无法解释为什么道德纯洁的伊尹、周公、孔子没有执掌这样的治理权,而执掌这种权力的人常常不仅“德衰”,而且还过得很滋润,只能搬出天命来作敷衍。为推行仁政,儒家又将周朝的“以德配天”思想发扬为“德主刑辅”理念,同时也努力向皇帝“责难陈善”,以求完善天子人格,实现仁政。孔子以仁释礼,游说各路诸侯实行“仁政”。孟子提倡“王政”,提出了比礼更具体的制度,认为统治者应当“省刑罚,薄税敛”,而且要实行“井田制”,“制民之产”,让每个农户都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保障温饱。“王政”即“王道”,与法家提出的“霸道”相对,反对暴力压迫,倡扬道德教化。但是儒家的温情脉脉背后却是逻辑上的千疮百孔,如此一来,理想的现实化建立在了现实的理想化基础上,形成了黄仁宇先生所谓的“金字塔倒砌”结构,也就是先造成理想上的公式(礼乐典章),“以自然法规的至善至美,向犬牙相错的疆域及熙熙攘攘的百千万的众生头上笼罩着下去”[21],天子借此自然法的至善作为其权威的背景,而官僚也借此治理百姓。“有时自知至美至善事实上不可能,宁可在实质上打折扣,表面文章决不放弃,甚至以礼仪代替行政”[21]171,这样在制度上就常常出现以上级理想为原则,不以下级实情为准据的效果。
西方自然法迸发的民主理念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大自然思想,因源于理性主义的种子,所以具有一种追求真理的性格,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为这种思想的完善和实践带来了契机,17世纪英国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洛克将“主权在民”理念播撒入人民的心田,对“君权神授”观念形成极大冲击。到18世纪,自然法又在法国花开两支,形成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和卢梭的“天赋人权”思想。而贯穿整个古典自然法思想脉络的是社会契约论,这些理论最终推进宪政思想的发展。
五、结语
综合上述,儒家通过对天的道德化,赋予“天理”这一思想以自然法的意义。然而与西方国家自然法的发展不同,儒家的自然法的主要作用并没有发挥在启蒙民智上,更没有衍生出法治思想的支流。这既有前文所述的思想脉络上的关联,也有社会经济生活上的根源。儒生们毕生研习的“礼”,历史悠远,任何人只能主动去接受,而断无改造的可能。人伦关系在此越发清晰,等级秩序也不断强化。公意被消泯在无声无息的世代传承中,个人理性被消耗在应付周围的远近亲疏中,不过人的一生既是只围着一亩三分田转,生存和稳定压倒一切,对自由与权利的追求并不迫切。
儒家虽然倡导“天理”,但是却与个人自由绝缘。在他们看来,礼更接近自然法,理应比法律优先。礼所根植其中的宗法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伦理社会,个人的平等与自由必须服从家族利益和伦常观念,权利观念自是无法产生。儒家民本思想没有发展出“民主”,却发展出了“主民”,整个国家体制就是要为民作主,这一思想绵延至今深入国人骨髓。比如证券市场一遇跌宕,股民们就引颈盼望政府来“救”市,而老百姓受了委屈找到法院是希望法官为自己“作主”,甚至于不少村官也习以为常地认为自己就是父母官。总之,儒家因过于理想而抛弃了法,而法家则过于实在而只顾取宠于统治者。法治、宪政这些民主形式无法从中国本土的自然法资源中挖掘思想素材。
总而言之,中西方虽各有自然法思想的火种,但因地理、人文、社情等诸多因素的不同而发展出迥然相异的路线。西欧自然法以理性为起点,强调个人意志的自由,生发出了权利观念,进而孕育出“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论”及“人民主权论”,最终经“分权制衡”思想演化出宪政理念;而儒家自然法思想以天道为依托,目标在于恢复礼治秩序,维持差序格局,同时也对君主提出了很高的道德标准,以求保民而王,主张“仁政”、“王政”。与此同时,儒家也通过恪守礼乐典章的传统,对君王的恣意进行约束,彰显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入世品格。
参考文献:
[1]邓建华.儒家自然法思想及其启示[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1):48.
[2]道德经•二十五章.
[3]汉书•艺文志.
[4]论语•为政.
[5][9]程帆.我听冯友兰讲中国哲学[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2:48-49;52.
[6]诗经•商颂•玄鸟.
[7]论语•阳货.
[8]论语•季氏.
[10]范忠信.梁启超法学文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86.
[11]论语•里仁.
[12]盐铁论•刑德.
[13]孟子•离娄下.
[14]孟子•万章下.
[15]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0.
[16]中庸.
[17]论语•为政篇.
[18]礼记•大学.
[19]荀子•大略.
[20]孟子•离楼上.
[21]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域[M].北京:三联书店,2001:148-149.
The Idea of the
MA Yong
( of and Law, ,China):
takes “Tian Li” as the for of any norms,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their own and into it, “Li” as the best means of . This kind view of “Tian Li” is of law, “Li” is of law, , what the core of this view of is - , which the ’s power, could not equal to the west’s law idea.
Key Words: law; Tian Li; - ; rule of rite; rule of law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