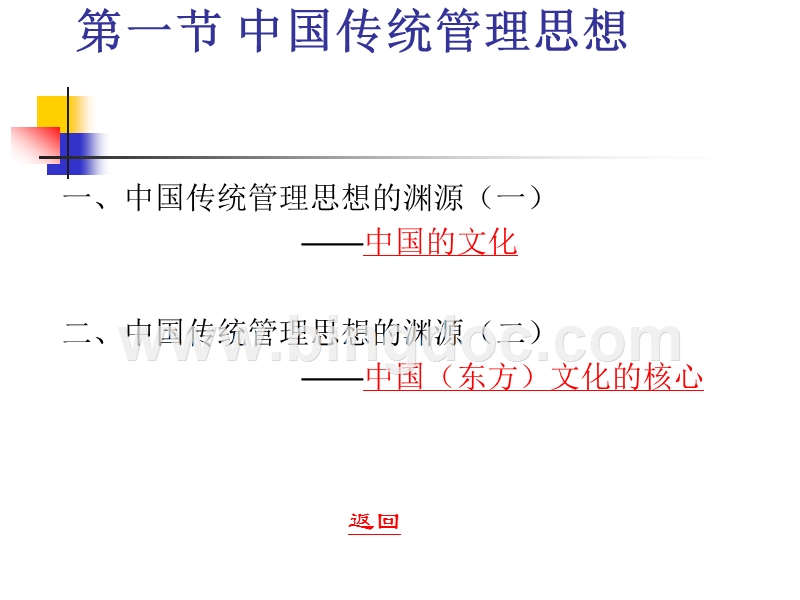《中国思想史研究》2022年卷探讨理学对玄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思想史研究》2022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第215-225页。
摘要/关键词
摘要:玄学确立了儒道会通的价值取向,并使“理”观念的哲学意义得到提升。王弼提出“至理”“理极”等观念,使“理”具有普遍意义而成为万物的本体。郭象提出“独化之理”说,使“理”成为万物生成的依据。但玄学还遗留了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本体论方面存在缺陷以及没有将儒、道思想在理论上统一起来。程颢沿着儒、道会通的价值取向,首先,在玄学“理”观念的基础上提出“天理”作为万物的本体,并进一步吸收、改造《周易》生成论思维,将天理同时作为万物生成的根据,使本体论思想更加完善;其次,通过生、仁互训,将儒家的仁德观念与道家的自然观念融入到“天理”本体中,从而最终在理论上实现了儒、道会通。
关键词:玄学;理学;程颢;王弼;郭象
关于理学与玄学,冯友兰指出:“道学的主题是讲‘理’,这是接着玄学讲的。”[1]又说:“由玄学一转语,便是道学。”[2]金春峰也认为“理学在某种意义上是玄学的继续”[3]。冯友兰、金春峰等指出了玄学与理学的联系,但没有对此深入探讨。程颢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者,其思想与魏晋玄学有密切关联。本文以程颢的天理思想为切入点,探讨理学对玄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一、玄学的学术贡献及遗留问题
玄学是魏晋时期流行的社会思潮,以《老子》《庄子》和《周易》为核心思想材料,以王弼、郭象等人为主要代表。玄学讨论的内容是社会现实问题与哲学问题的统一,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是名教与自然的矛盾,所探讨的哲学问题则是本体论问题。玄学的学术贡献以及未能解决的问题,对理学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一)玄学的学术贡献
玄学的学术思路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确立了儒道会通的价值取向。名教与自然是玄学中的重要范畴,分别代表儒、道二家的价值观。名教,一般指儒家礼教和道德规范。自然,一般指自身本然、自性状态。儒家强调礼治教化道家自然思想的内容和现实价值,道家则主张自然无为。汉末魏晋时期,社会黑暗,经学衰落,儒家名教异化为追名逐利的工具,人们开始习惯于放纵行乐,违礼之举大量出现,名教信仰产生危机。玄学的出现正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名教危机,正如学者高晨阳所说:“如何调整或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使双方获得协和与统一,成为玄学的中心课题。”[4]何晏、王弼等人主张“名教出于自然”,认为名教必须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郭象主张“名教即自然”,认为现实中的名教礼法是合乎自然的。无论是王弼还是郭象,都主张会通儒家之名教与道家之自然。
其次,王弼、郭象等玄学家提高了“理”在哲学史上的地位。钱穆先生指出:“此一理的观念之郑重提出,若谓于中国思想史上有大功绩,则王郭两家当为其元勋。”[5]在先秦道家文献中,“理”只是事物的分殊之理,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老子》中并无“理”字;《庄子》对“理”字有所运用,如“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庄子·养生主》),这是庖丁对解牛的描绘,此处“理”指牛体的生理结构;再如“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庄子·渔父》),此处“理”是指人的自然本性。《庄子》中的“理”是附属于“道”的观念,指个别事物的自然本性或规律,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王弼提出“至理”“理极”等观念,使“理”具有普遍意义,从而提升了“理”的哲学意义。王弼认为虽然具体事物各有其理,但是众理可以会归为一。他说:“夫事有归,理有会。故得其归,事虽殷大,可以一名举;总其会,理虽博,可以至约穷也。譬犹以君御民,执一统众之道也。”[6]王弼所谓“理虽博,可以至约穷也”,是说可以把广博的事物之理会归为“执一统众”之理。“执一统众”之理,即王弼所谓“至理”或“理极”。他说:“我之教人,非强使人从之也,而用夫自然。举其至理,顺之必吉,违之必凶。”(《王弼集校释·老子道德经注·第42章》,第118页)又说:“能尽理极,则无物不统。极不可二,故谓之一也。”(《王弼集校释·论语释疑·里仁》,第622页)王弼强调“至理”“理极”的重要性《中国思想史研究》2022年卷探讨理学对玄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认为顺应“至理”、把握“理极”,就能统御一切事物。因此,“理极”“至理”已经不再是具体事物的分殊之理,而是天地间一切事物运行的普遍原则。

在郭象的思想中,“理”概念的哲学意义更加丰富。首先,郭象吸取了王弼的“至理”观念,使“理”具有普遍意义,如:“故理至则迹灭矣。今顺而不助,与至理为一,故无功。”[7]“是非死生,荡而为一,斯至理也。至理畅于无极,故寄之者不得有穷也。”(《南华真经注疏·内篇·齐物论注》,第56页)以上“至理”都具有普遍意义。其次,郭象使“理”成为万物生成的依据。郭象反驳“有生于无”的说法,提出了“独化论”,指出:“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罔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南华真经注疏·内篇·齐物论注》,第57页)郭象认为万物皆“独化于玄冥”,而不是源于造物者,如陈荣捷先生所说:“郭象对造物者的否认是十分彻底的。”[8]他进而提出“独化之理”作为万物生成的依据,他说:“推而极之,则今之所谓有待者,率至于无待,而独化之理彰矣。”(《南华真经注疏·杂篇·寓言》,第545页)又说:“卒至于无待,而独化之理明。”(《南华真经注疏·内篇·齐物论注》,第57页)郭象认为事物的生成不必依傍他物,只凭“独化之理”即可。“独化之理”即事物不依傍他物而独自生成的原理。郭象把“独化之理”作为万物生成的依据,从而使“理”概念的哲学意义得到进一步的提升。综上,王弼提出“至理”“理极”等概念,使“理”具有普遍意义。郭象提出“独化之理”说,使“理”成为万物生成的依据。玄学使“理”概念的哲学意义得到了很大提升,为理学“天理”概念的提出做了理论铺垫。

(二)玄学遗留的问题
玄学的理论体系并不完善,在以下两个方面较为突出:其一,玄学的本体论还有待发展。余敦康先生曾指出:“在中国的天人之学中,讲本体不能脱离生成,生成应该是本体的一个本质属性。”[9]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本体论与宇宙论往往是融合在一起的,但玄学于此还有不足。王弼将“无”作为万物的本体,但在解释万物生成时遇到了理论困难。王弼吸取《老子》“有生于无”的宇宙论,指出“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王弼集校释·老子道德经注·第1章》,第1页)。在王弼的思想体系中,“无”和“有”既是体用关系,又是母子关系。然而,“有生于无”命题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无”究竟是什么?这是无法正面回答的。如果说出它是什么,它就不再是“无”而变成“有”,如果不对它进行解释,又难以将它作为宇宙万物的起点。将不可言说的“无”作为万物的起点,必然有诠释上的困难。王弼“有生于无”的宇宙论,遭到了诸多反对。裴頠《崇有论》就对王弼大肆攻击,指出“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10],裴頠认为绝对的“无”不能产生任何东西。在裴頠等人的理论攻击下,王弼的理论相形见绌。
郭象否定了“道”的万物本源意义,提出“独化论”的观点,认为万物不依傍于他物而自然化生。“独化论”即郭象的宇宙生成论。唐代时期,郭象的“独化论”遭到了佛教信徒的批评。宗密云:“又言万物皆是自然化生,非因缘者,则一切无因缘处悉应生化,谓石应生草,草或生人,人生畜等。”[11]宗密指出如果万物都是自然化生的,而不是因缘和合而成的,那么在一切不存在因缘关系的地方,都应该有生成化育现象,比如石头中长草,草生出人等等,可事实并不是如此。佛教对郭象生成论的批评是有见地的,郭象的“独化论”忽视了事物之间的联系,没有注意自然中固有的生成规律。此外,郭象的“独化论”也没有解释世界的源头,世界从何而来仍然是神秘不可知的。与佛教以现实世界为虚幻有所不同,中国儒、道二家都承认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因此,他们必须为现实世界的来源做出说明。
其二,虽然玄学主张统一名教与自然,但他们并没有在理论上将二者统一起来。王弼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末,主张“崇本息末”,显然是将自然置于名教之上。郭象的“名教即自然”也有不足,他认为现实中的一切名教都是符合自然的,呼吁人们安时处顺,思想走向消极。在郭象的思想中,即使是“吃人”的礼教,也是符合自然的。对于解决现实中的名教异化问题,郭象的理论意义不大。因此,虽然玄学家提出了统一自然与名教的主张,但并没有在理论上将二者贯通起来。玄学的理论缺陷对于理学思想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正是理学的理论出发点。以程颢为代表的理学家们,将继续探讨玄学悬而未决的问题。
二、程颢对玄学本体论的发展
鉴于玄学在本体论方面存在的不足,程颢在玄学“理”观念的基础上提出“天理”作为万物的本体,并吸取《周易》的生成论,将“天理”作为万物生成的依据。通过这样的改造,“天理”既是万物的本体,又是万物生成的依据,从而成为最高的哲学范畴《中国思想史研究》2022年卷探讨理学对玄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使本体论思想更加完善。
首先,程颢继承并发展了玄学的“至理”概念,提出“天理”作为万物的本体。程颢说:“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来,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是他元无少欠,百理具备。”[12]程颢在此指出天理具有“百理具备”的特点,不是指具体事物之理,而是包含了万事万物之理。程颢的“天理”与王弼所谓“夫事有归,理有会”的会归之理一致,都是可以“执一统众”的普遍原则,是万事万物所共同遵循的原理。
其次,程颢论“天理”不仅统摄事物,也统摄人性。玄学家所谓“理”多指事物之理,而没有指向人的本性,如王弼所谓“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王弼集校释·周易略例·明彖》,第591页),郭象所谓“物物有理,事事有宜”(《南华真经注疏·内篇·齐物论注》,第44页),等等。程颢“天理”则统摄了人的本性。他说:“‘万物皆备于我’,不独人尔,物皆然。都自这里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则能推之。虽能推之,几时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几时减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铺放着。”(《二程集》,第34页)此处“万物”与“百理具在”相对应,指天理而言。程颢指出“‘万物皆备于我’,不独人尔,物皆然”,意谓人和自然万物皆是天理本体的呈现,因此,人的本性和万物的本性皆源于天理这一根据。和玄学相较,程颢认为人的本性也是“天理”的呈现,从而使“天理”的本体意义进一步丰富。
再者,程颢所谓“天理”不仅是万物的本体,而且是万物生成的依据。在郭象的思想中,就有把“独化之理”作为万物生成依据的观点,使“理”统摄生成意义,但程颢并未继承玄学的宇宙论,而是吸收了《周易》的宇宙论。《周易》是玄学的重要经典,被列为“三玄”之一,但《周易》的宇宙论并没能引起玄学家们的重视。王弼“有生于无”的宇宙论和郭象的“独化论”都遭到了当时或后来学者的批评。程颢吸收《周易》的宇宙论,认为包含人类在内的宇宙万物皆是天地阴阳二气变化而来的。他说:“天地阴阳之变,便如二扇磨,升降盈亏刚柔,初未尝停息,阳常盈,阴常亏,故便不齐。譬如磨既行,齿都不齐,既不齐,便生出万变。故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二程集》,第32-33页。)程颢认为万物皆出于天地阴阳二气之变,由于阳常盈、阴常亏,所以才生出不同的自然万物。又说:“人在天地之间,与万物同流,天几时分别出是人是物?”(《二程集》,第30页)程颢认为天并未有意区分人和自然万物。人和自然万物一样皆源于天地阴阳二气,皆是阴阳二气大化流行的产物。以《周易》解释万物化生是北宋理学家的共同特点,不仅程颢如此,周敦颐、邵雍、张载等人也是如此。但程颢不像邵雍、周敦颐那样以“有”“无”解释《周易》,也不像张载那样以“清虚一大”言说《周易》,而是以“天理”解释《周易》,将“天理”作为万物生成的依据。

关于天理是阴阳二气变化的依据,程颢还说:“易是个甚?易又不只是这一部书,是易之道也。不要将易又是一个事,即事尽天理,便是易也。”(《二程集》,第31页)程颢指出“易”不只是一部书,而且是“易之道”,“易之道”即事物运动变化所遵循的原理。在《周易》中,“易”本指阴阳二气的变易,程颢所谓“易之道”,即阴阳二气变易所遵循的依据。他还说:“夫天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岂可逆哉?”(《二程集》,第125页)程颢认为万物存在长、短、大、小等参差不齐的现象,都是依据“天理”而生成的。长、短、大、小等是万物存在的形式,形式决定于“天理”,因此,“天理”就是“易之道”,即万物生成的根据。
和玄学相较,程颢提出“天理”作为万物生成的根据具有进步意义。首先,他改良了王弼“有生于无”的宇宙论。在“有生于无”的理论下,“无”和“有”既是体用关系,又是母子关系。可是,在母子关系中,“无”如何产生“有”这是难以回答的。程颢“天理论”则吸收道家的体用关系而摒弃其母子关系,“天理”是“气”的运行依据,而非“气”之母。其次,程颢回应了宗密等佛教信徒对郭象“独化论”的批评。郭象“独化论”认为万物独自生化,否认事物之间的因缘联系,事物从何而来成为“不可知论”,招致佛教信徒提出“草或生人,人生畜”的质疑。程颢将“天理”作为万物生成的根据,认为万物的生成是由天理决定的,万物的长、短、大、小等参差不齐的现象也取决于“天理”。郭象“独化论”的理论缺陷在于缺乏支配万物生成的根据,程颢将天理作为万物生成的根据恰恰解决了郭象的理论不足。
综上,程颢继承并发展了王弼、郭象的“理”概念,提出“天理”作为万物的本体,并以“天理”统摄人性,丰富了本体论意义。他还抛弃了玄学的生成论,吸收《周易》的生生之论,认为宇宙万物以阴阳二气作为物质基础,以“天理”作为生成依据。通过以上构建,“天理”成为最高的哲学范畴,是宇宙论与本体论的圆融结合。程颢对“天理”本体的构建,是对玄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实质是改造了玄学的“理”观念,并与《周易》的生成论融合。
三、程颢对儒、道会通理论的建构
玄学确立了儒道会通的价值取向,但王弼、郭象等人并未真正在理论上实现二者的会通。程颢沿着玄学的会通精神,建构了较为完善的儒、道会通理论体系。理学最重要的“天理”观念就体现了儒家精神与道家精神的会通。程颢的天理论是在玄学“理”观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鲜明地继承了玄学的自然价值观。譬如,程颢说:“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二程集》,第121页)此处说明了“理”的自然意义。程颢还说:“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二程集》,第125页)程颢在此明确肯定了天道的自然特征。在程颢的思想体系中,“理”和“道”互通,此处“天道”即“天理”。程颢又说:“圣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异端造作,大小大费力,非自然也。”(《二程集》,第142页)这段材料是程颢对佛教的批评,他认为佛教造作而不自然,圣人循理而自然,再次肯定了“理”的自然意义。玄学的“理”观念是程颢“天理”观念的基础,因此,自然观念是程颢“天理”观的基本内容。程颢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把儒家的价值观融入到天理观念中,从而在理论上实现了儒、道价值观念的统一。程颢作了如下理论建构:
首先,与玄学将“名教”作为儒家的基本价值有所不同,程颢将“仁”作为儒家的基本价值。程颢对“仁”非常重视,著有《识仁篇》,曰:“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二程集》,第16页)程颢将“识仁”作为学者修身之要旨,把“仁”当作全德,认为义、礼、智、信等都属于仁的内容。和玄学相比,程颢对儒家精神有更深刻的理解,因为“仁”比“名教”更能体现儒家的基本精神。“仁”与“名教”的关系,即《论语》中“仁”和“礼”的关系。在孔子的思想中,“仁”是比“礼”更加重要的概念。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礼仪制度遭到了践踏,譬如“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季氏旅于泰山”(《论语·八佾》)[13]等,孔子对此发出感慨:“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孔子认为假如没有仁,礼和乐是没法运用的。由此可见,孔子认为“仁”比“礼”更加重要,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孔子言礼,重在礼之本,礼之本即仁。”[14]程颢重视“仁”而非“名教”,是对玄学理论的发展,因为“仁”比“名教”更符合儒家的基本精神。
其次,程颢将“仁”与“生”互训,使“生”具有仁德意义。在《周易》中就有将“生”解释为“德”的先例,譬如“天地之大德曰生”“日新之谓盛德”(《周易·系辞》)等。程颢将“生”“仁”互训,是对《周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二程集》,第120页)在程颢看来,万物的生机最可观,这就是首要的善,也就是所谓仁。万物的生机就是“仁”,于是“生”就有了仁德意义。程颢又说:“医书言手足萎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二程集》,第15页)在这段材料中,程颢没有明确将“仁”释为生机,但却有这层寓意在其中。他赞同医书所说手足萎痹为不仁,又说“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道家自然思想的内容和现实价值,“不属己”便是失去知觉,缺乏生机;与此相反,“仁”则可解释为有知觉,有生机。他又说:“切脉最可体仁。”(《二程集》,第59页)这依然体现出了“仁”的生意,因为切脉时能真切地感受到脉搏的跳动,此乃生命的体征、生机的体现。他还说:“观鸡雏,此可观仁。”(《二程集》,第59页)这同样表达了“仁”的生机之意,“鸡雏”即刚破壳而出的小鸡,生意盎然,朝气蓬勃,程颢认为“此可观仁”,也体现出了“仁”的生生之意。总之,通过“生”“仁”互训,“仁”有了生生不息之意,“生”则具有了仁德意义。
最后,以“生”为桥梁,沟通“天理”与“仁”。“生”除了具有仁德意义外,还是“天理”本体的特征。“天理”是程颢思想中的最高范畴。程颢以阴阳二气作为万物的物质基础,以“天理”作为万物的生成依据,而“天理”的特征就在于生生不已。程颢说:“‘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亦是万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为道。”(《二程集》,第30页)这是程颢对《周易》“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的解释,认为生生不息是万物的本性,并指出天道的特征就在于生生不已。程颢又说:“‘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二程集》,第29页)程颢再次指出生生不息就是天道,天道只在于生生不息,因为能够继承此生生之理就是“善”。此处“生理”即“天理”。综上,天理即生生不息之理,“生”是天理本体的特征,而“生”又具有仁德意义,于是,天理本体也就有了仁德意义。
程颢通过“生”建立仁德与天理本体之间的联系,为仁德和天理之间架构起一座桥梁,于是,仁德就成了天理本体的特征。通过这样的构建,天理本体不仅含有道家的自然意义,还兼具儒家的仁德意义。程颢在本体层面实现了自然与仁德的统一,解决了玄学没能完成的儒、道会通问题。程颢会通儒道二家所依据的重要典籍是《周易》。《周易》虽为“三玄”之一,但《周易》的宇宙论、“天地之大德曰生”、“日新之谓盛德”等理论,都没能引起王弼等人的足够重视。程颢则沿着玄学的辙迹,进一步吸取《周易》思想,最终完成了儒、道会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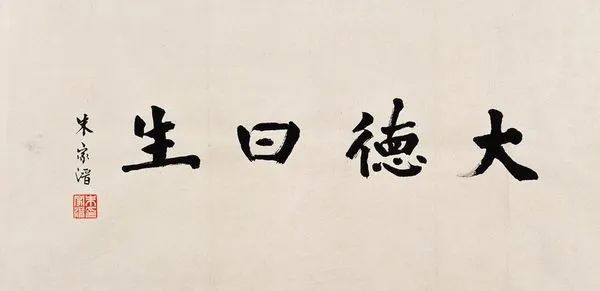
(书法:大德曰生︱图片来源于网络)
四、结语
理学与玄学是具有内在联系的。二者的时代背景有所不同,但思想主旨一致,都是要会通儒、道二家学说。玄学面对的是儒家名教异化的问题,因而援引道家以救治儒家之弊。理学面对的是佛教文化的冲击,因而援引道家共同对抗佛教。殊途同归,不同的时代问题使玄学和理学拥有共同的思想主旨。
理学思想在形成中解决了玄学悬而未决的问题。王弼和郭象的本体论还有所不足,程颢以“天理”统摄王、郭的“道”“至理”“独化之理”等范畴,使“天理”成为内涵丰富的最高哲学范畴。实现儒、道会通,是程颢对玄学的又一重要发展。儒、道二家在先秦时就有思想交锋,儒家指责道家“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若以道家的视角看儒家,则是“蔽于人而不知天”。玄学欲去两短而取两长,确立了儒、道会通的价值取向,但并没有完成二者的统一。程颢沿着玄学指出的方向,将儒家的仁德观念和道家的自然观念融入到“天理”观念中,在理论上完成了儒、道会通,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发展基础。
在经典诠释和观念使用方面,理学和玄学也有延续性。玄学与理学均重视对《周易》的研究与诠释,并表现出前后相继的学术理路。《周易》是“三玄”之一,程颢在建构宇宙生成论、赋予天理仁德意义时,较多地借鉴了《周易》的思想。此外,玄学与理学都注重对“理”观念的运用,从先秦道家到魏晋玄学,再到宋明理学,“理”观念一脉相承,其哲学意义层层递进,最终成为最高的哲学范畴。玄学为理学的产生做了很多理论准备工作,如果没有玄学的理论铺垫,理学的产生将不会如此顺利。
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二程著述辨析及思想关系研究”(项目号:)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2] 冯友兰:《关于〈美的历程〉的一封信》,《三松堂全集》第13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82页。
[3] 金春峰:《从比较联系中考察玄学》,《文史哲》1985年第4期。
[4] 高晨阳:《自然与名教关系的重建:玄学的主题及其路径》,《哲学研究》1994年第8期。
[5] 钱穆:《庄老通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31页。
[6] 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论语释疑·里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22页。
[7] 郭象注,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点校:《南华真经注疏·内篇·逍遥游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道家自然思想的内容和现实价值,第9页。
[8] 陈荣捷:《中国哲学文献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05页。
[9] 余敦康:《魏晋玄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页。
[10] (晋)裴頠:《崇有论》,《晋书》卷三十五《裴頠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46页。
[11] 董群译注:《原人论全译》,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89页。
[12]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页。
[13] 八佾是六十四人之舞,只有天子才能用,而季氏只是大夫,只能用四佾,因而僭礼。《雍》是天子之礼,季氏作为大夫不该擅用。只有天子和诸侯才有资格祭祀名山大川,季氏作为大夫没有资格祭祀泰山。以上皆是僭礼行为。
[14] 钱穆:《论语新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4页。
图文编辑︱黄 熙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