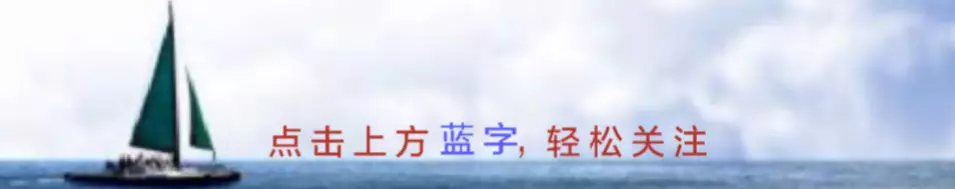宋朝的士大夫既是当时文化生活的主体,在政治上也掌握了相当大的话语权。与唐朝相比,这个时候的士大夫从来源上和以往大不相同。由于唐末气势浩大的农民起义,门阀名流在兵荒马乱中已被摧毁殆尽;五代更迭,武人掌权,名流子弟不过是这些军阀用来装点朝堂的门面。而宋朝士大夫更多通过科举从民间走到朝堂,作为读书人,他们比唐朝时期的文人掌握更大的政治权力;作为重要的统治阶层,他们身上的文人色彩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重。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下文简称《朱熹的历史世界》)中要展现的正是宋朝文人所特有的政治文化。本书的主标题为“朱熹的历史世界”。按余英时的话来说,这本书是“尽量根据可信的证据以重构朱熹的历史世界”。这个“历史世界”我们可以理解为在相关文献整理后,通过历史研究,形成以朱熹为第一视角的社会面貌。朱熹生活在南宋时期,此时宋朝士大夫政治已经发展成熟了,朱熹本人作为著名的理学家,在宦海浮沉半生,自然属于士大夫群体。然而,在学界以往对朱熹的关注更多集中在其理学家的身份上,对他本人的认识往往依附在对他理学思想的认识上。作者在书中则完全颠覆了这种认识,将朱熹理学家的身份与士大夫的身份重合起来,而这个关键就在副标题中的“政治文化”。
一、著作的主要内容《朱熹的历史世界》分为上下两册,上册是通论,探讨的是北宋以来儒学的发展和士大夫政治种种政治原则的确立,是这个“历史世界”的大背景;下册是专论,作者详细考证了朱熹所处政治环境对其思想的影响和朱熹等一批理学家在政坛上历经几朝的努力活动。贯穿这两本的线索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作为儒家“內圣”之学的道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另一条是北宋以来的儒学家们“致君行道”的“外王”之路。朱熹被公认为是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是道学的代言人。而在南宋孝、光、宁时期,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家们积极参与朝堂政治活动,形成一股政治力量。而在庆元时期以“禁伪学”为名的政治风波,朱熹更是处于斗争漩涡中心。可以看到这两条线索最终在朱熹身上交汇,并展现完整的士大夫政治文化面貌。(一)通论通论包含七个章节,是对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总体把握,也是朱熹历史世界的大背景。在开篇绪说中,作者首先解释了道学体系中“道学”、“道体”、“道统”几个概念。作者认为所谓道学是北宋儒学的重要部分,“道体”只是道学抽象的一端,朱熹本人也认为学者不必以“道体入手”。道学的主要内容还是集中在儒家所言“內圣”中的格、致、诚、正、修和“外王”的齐、治、平这些方面。
朱熹的道统论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圣人统治天下,德位兼备,他们之间传授“道统”;而孔、孟之时,统治者德不配位,而圣人们只能传承“道学”。而朱熹提出道统论的目的就在于用“道统”来约束君主,使之向三代圣人看齐;用“道学”来提高士大夫地位。随后,作者指出宋代儒者对儒学的定位是重建“三代之治”的学问,他们随时代的变迁发展儒家学说。作者将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古文运动、王安石新学时期、后王安石时期。而道学也在古文运动“重建统治秩序”的呼声中孕育,在应对王安石新学的挑战下成型,在朱熹等一批理学家的努力下发展成型。在第一章“回向‘三代’——宋代政治文化的开端”中,作者先是列举宋以后史学家对宋朝的评价,这些评价大多把汉、唐、宋称之为“后三代”。鉴于宋朝并不以政治武功著称,作者认为这是推重宋朝在文化史的表现。而在宋朝士大夫留下的相关记载中,不断提到“三代之治”。王安石变法时,也希望神宗法三代贤君之意。从仁宗时开始,士大夫群体不论政治立场如何,动辄引“三代”为证,可见这确是宋朝政治文化的特色,也是宋朝士大夫政治活动的终极目标。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探讨宋代“士”的政治地位。宋朝士大夫地位提高是明白无误的事实,作者也肯定了这一点。
宋朝是通过政变建立起来的,一开始就缺乏深厚的社会基础,统治者也害怕武将颠覆新政权,再加上士阶层自身潜布各地,两者都有相互支持合作的需求。而这一过程是通过科举制度的完善来推动完成的。作者将宋朝科举与唐代、五代进行对比,突出了宋朝对科举的极度重视。通过科举从社会各阶层跻身政坛的士大夫们得到了朝廷的优渥对待,自然也激发并加深了他们对国家的认同。随后三章描述的则是士大夫阶层与皇权之间的互动。范仲淹以后,“以天下为己任”意识在士大夫群体中广泛传播。作者认为原因在于进士们多来自民间,并且总量很多,在儒学复兴的大潮流下,特别关注现世秩序。无论是范仲淹设置“义庄”以“礼”化“俗”,还是王安石在中央主持“新法”都是其具体表现。而文彦博所言“为与士大夫治天下”正是在皇权下的士大夫政治形态。在神宗、王安石和文彦博对话中看来,他们似乎都视为理所应当。与西汉贾谊、唐朝韩愈认为臣子只是奉君主命令治理天下相比来说,作者指出程颐所言君臣“同治天下”更体现宋朝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意识。而最能代表士大夫群体与皇帝“同治”天下的便是宰执大臣了。作者举神宗力排众议一力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例子,来说明在此之前,依然是自秦朝以来的“君尊臣卑”的局面。
王安石变法中“三司条例司”的设置说明王安石此时拥有的非常相权。作者认为神宗之所以甘愿给予王安石这样大的权力,正是他们拥有共同的政治理想,渴望重建“三代之治”。神宗与王安石君臣之间的相知相遇也被朱熹认为是“千载难逢”。王安石的非常相权从正面上象征着士大夫拥有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权力,从反面来说也为后来权相把权留下暗路,作者在第五章提到的“国是”其一。“国是”简而言之就是皇帝与士大夫们确定以后大致的政治方向,这个“国是”一旦确立,便对双方都有相当大的约束力,不得任意更改。神宗时期的“新法”、哲宗元祐时期的“更化”和绍述年间的“绍述”、徽宗时期的“建中”等等都为人所熟知的“国是”。作者在下册专论中还详细考证了南宋数朝的“国是”。第六章则又回归到儒学的发展历程。作者遵从朱熹的说法,将在二程之前的宋初三先生认作宋朝儒学复兴的起源。这三位先生虽未涉及“性命道德”方面,却在“说经”时,不离“推明治道”的主旨。可见在朱熹眼中,儒学复兴在于对“重建秩序”的追求。这种理念自然也影响了王安石和二程。王安石著《三经新义》也有从儒学经义中寻求“二帝三王为天下家国之意”的目的在里面,这也是其变法的精神动力。王安石变法之初,程颢、苏辙这批士大夫都曾积极参与,这表现出儒学复兴后,士大夫对“重建秩序”的追求由理想迈向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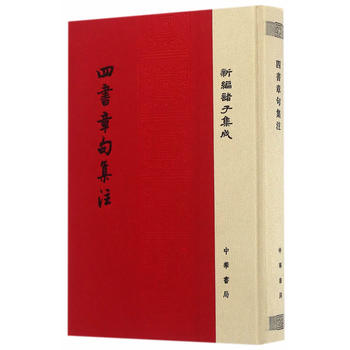
第七章中,作者进一步分析士大夫内部的分化。这种分化表现在朝堂之上就是党争。作者把两宋的党争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仁宗时期的范吕党争,这一时期,皇帝超脱于两派之上,仍具有最终裁断之权。而在熙宁以后,神宗和王安石将“国是”法度化后,不但士大夫内部因学术思想和政治观点分分化日益明显,而且皇帝因与其中一派共定国是,也参与到党争之中,其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各党派互相倾轧。而到朱熹的时代,道学在朝堂中终于有了自己的政治势力,接近获得“致君行道”的机会。作者把当时反道学的一派称之为“职业官僚型”士大夫,他们在孝、光、宁三朝中掀起了三次反道学高潮,与“道学型”士大夫反复较量。而朱熹本人则处于两党斗争的中心,最终“道学”成为“职业官僚型”士大夫打击政敌的一大名目,成为“伪学”,遭到封禁。(二)专论正如下册绪说中所言,相比上册论述朱熹历史世界的整体背景,下册是朱熹所处时代政治文化的专论。作者将主要论述对象分为三类:“道学型”(与理学互训)士大夫群体、“职业官僚型”士大夫以及皇权集团。从朱熹孝宗即位之初进入政坛,到宁宗庆元党禁的这一段时期,正是他全部的政治生涯,也是专论大体上的时间范围。第八章则专论理学家们的政治取向。
作者并不认为南宋理学家们只是专心于“内圣之学”,并发现他们在孝、光、宁三朝政坛里异常活跃。但“內圣”与“外王”问题上存在内在紧张问题,对二者偏重不同,其行为模式也不同。但理学家总体来说无论偏重,都坚持两者相互配合。儒学在这一时期进入理学时代,由“內圣”转入“外王”是这一阶段政治文化的特色,而理学家们奉行的是传统儒学观念中的“得君行道”。作者通过分析朱熹、陆九渊、张栻、吕祖谦的例子来得到南宋理学家“得君行道”的一般形态(轮对、登对),并进一步推论其与理学家群体的关系。书中所言的“得君行道”,指的是理学家在“知见”层面影响人主,使得人主主动“行道”。这虽然属于“外王”领域,但理学自身却必须要在发展和完善“內圣”这一范围。第九章中作者通过几个政治事件件来表现权力世界中的理学家们。理学家们的“外王”理想是和孝宗的“恢复”之志联系在一起的。但孝宗在位时,高宗仍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士大夫在朝堂的势力主要是主张安静的“官僚型”士大夫,这也是理学家们的主要对手。在淳熙十三年陆九渊第二次轮对前夕被逐一事中,作者分析当时局势,认为当时正处于官僚集团对道学的反攻之际。作者对事件中官僚集团的动机和手法的考证也十分精彩。
而刘清之以“道学自负”的罪名被罢免知州的事件反映了双方在地方行政系统里的斗争。朱熹则透过此案中“道学”一词,便明白官僚集团日后便可借此扩大打击面来攻击任何理学之士了。这些案件都发生在官僚集团领袖王淮执政期间。而淳熙十五年高宗去世,孝宗便借故将王淮罢免了,并以亲近理学家的周必大为首相。理学之士在权力世界迎来转机。前面所言的“得君行道”集中显现在孝宗一朝,这也使作者不得注意孝宗与理学家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第十章的主要内容。孝宗在高宗去世之后,便又谋图“恢复”,便把这理想寄托在要求改变“安静”现状,重建秩序的理学之士身上。孝宗晚年的政治部署也是朝堂上的一次大变动。大体而言,孝宗在内禅之前战国儒家思想为士大夫政治奠基,委任周必大为首相以过渡,并让同样与理学界关系密切的留正为副;退位后,此前他一直想大用的赵汝愚终于也登上执政之位。而赵汝愚对理学的推崇人尽皆知,在他执政期间,不少理学之士进入朝廷,其中就包括朱熹。作者在此处也详细论述了朱熹在朝这四十天的经历。孝宗晚年的另一大部署就是擢用理学型士大夫,诸如尤袤、薛叔似、詹体仁、刘光祖、黄裳、罗点等人因此得以进入权力中心。作者详细考证以上众人的学承与交游关系,确认其都属于理学集团。
而理学集团在这一时期的布局主要是依靠荐士和重整台谏展开的。通过这两种方式,理学集团在朝堂中的力量和声势大大加强了。第十一章分析的是官僚集团的起源和传承。作者首先明确其与理学集团的分歧。相比于理学集团要求以“共治者”身份参与秩序重建的自觉,官僚集团更倾向于保持现状,这导致两者不可能不发生冲突。作者将官僚集团的起源追溯到淳熙十年陈贾“请禁伪学”,这是因为其任监察御史正是王淮所安排,其打击对象虽是朱熹却上升到“道学”层面,并以朋党定义理学集团,理学集团与官僚集团两极分化由此开始。这一时期官僚集团既包括宰执中的王淮,也包括以陈贾为代表的台谏,以及给舍、贰卿等一大批职业官僚。在王淮罢相后,这一集团在朝中势头渐弱,但力量依然可观。光、宁时期战国儒家思想为士大夫政治奠基,官僚集团则转为和代表皇权的近幸(光宗时的姜特立、宁宗时的韩侂胄)合作,局面又逆转过来了。最后,作者分析了官僚集团中刘德秀和皇权近幸姜特立的相关材料,考察其中两者与理学士大夫交往的片段,来证明官僚集团在着与理学集团历经数朝争斗过程中的传承。最后一章从皇权角度分析这场政局大变动。作者将高宗去世后的一系列行为称之为“三部曲”(“三年之丧”、“太子参决”、“内禅”)。

这些举动对于一个刚作了“恢复”部署的皇帝而言是非常奇怪的。作者借心理学的相关知识对其进行分析了孝宗的成长经历。从孝宗还是孩童被选入宫中之时,一直到高宗去世,孝宗一直在高宗的阴影之下如履薄冰,其政治抱负也不得施展。他对高宗怀着既感激又怨恨的复杂心理,“三年之丧”正是这种心态的表现,一方面表达了哀思,一方面也是对绍兴七年高宗当年行短丧的批评与反抗。而随后禅位给光宗的作法,在作者看来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既能合乎“古礼”,无违父志宋朝的士大夫的历史世界:朱熹的“政治文化”,又能像当初高宗控制自己一样控制光宗完成部署。但光宗毕竟不如孝宗坚韧稳重,志向远大,竟然忍受不了孝宗的压力而落下了心病,与孝宗关系破裂,不再“定省如故”,使得孝宗对朝堂的影响大大减弱了。待孝宗、光宗去世后,宁宗继位,理学集团“得君行道”的机会变得越发渺茫了,随后的庆元党禁为孝宗的部署彻底画上了句号。二、史识创新本书最大的史识创新就在于“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使用。作者对其作了两种解释,其一“相当于英文‘ ’......大致指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行动的风格”,其二则“兼指政治与文化两个互别而又相关的活动领域”。宋朝在政治制度史上有很多鲜明的特色,而作者显然认为士大夫政治才是使宋代得以比隆汉、唐的真正原因。
宋朝人自己最引以为豪就是他们在儒学道德上的成就远超汉、唐,士大夫们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宋朝士大夫政治的最高目标就在于恢复“三代之治”,在这批深受儒学复兴影响的士大夫们看来汉唐的“功利”远不如“三代之治”那样直指人心,意义深远。随着宋朝士大夫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主体”意识逐渐觉醒,希望构建一个与皇帝“同治天下”的政治理想模式。这一点在王安石变法以后表现得十分清晰。大臣“以道进退”,皇帝与大臣“共定国是”正是宋朝政治所独有的现象。作者对“国是”这一宋朝政治新因素的把握更是让人叹为观止。作者认为“国是”的出现表明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权力得到皇权一定程度的认可。作者在书中通过梳理神宗以来“国是”的变动情况,准确地把握了政治取向的变动,这对解释孝宗时政局及其晚年布局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将“皇极”作为“国是”的假设,对其在孝、光、宁三朝影响进行论述,可谓对“国是”概念的认识上独树一帜。但作者也提到“国是”在党争中发挥的负面作用,“国是”的出现本身就代表士大夫内部意见的分化,而且这种分化的结果是一方以绝对的皇权、法度来压过另外一边。每一次“国是”的变动都是朝堂上的大震动,而党争中往往有人会借“国是”肆意打击政敌。

以上所言有关宋朝政治上的特点,当是作者所指“政治文化”的第一层含义。本书对理学世界的认识也可谓是别出心裁。作者通过对朱熹对道学基本概念和起源的解释,建立起一条有关宋朝儒学发展的完整脉络。在这条脉络中,作者将儒学分为三个阶段(古文运动时期、王安石时代、理学时代),并且用“政治文化”这个概念,将儒学与士大夫的政治活动联系起来,古文运动时期儒者对儒家秩序重建的呼声;王安石立“性命道德”之说,法“二帝三王天下家国之意”推行新法;理学家们艰难的“致君行道”之路都体现出这一点。以往学者对理学家的认识通常仅停留在其学术和教育工作,而忽视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努力和作用;对道学的定位接近只谈“心性义理”的思辨性哲学。作者将这种认识归之于之前传统道学认识已经经历过两次“抽离”:首先是将道学从儒学中抽离出来,接着又把“道体”从道学中抽离出来。于是,我们往往把理学家们有关“道体”的认知当作是他们毕生追求的道学。而作者却能透过理学家的著述和他们在史料记载中的相关政治活动,推导出理学家的政治取向和政治处境,将他们理学家和士大夫双重身份合二为一。这就是标题中所言的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第二层含义。然而,尽管作者尽可能详细地分析宋朝士大夫各学派观点,但其重点主要还是集中在儒学三个阶段之间的脉络梳理宋朝的士大夫的历史世界:朱熹的“政治文化”,对王安石新学与道学思想内涵上的区别并没有太深入地对比,只是援用佛教在北宋的新变动对两者“性命道德”问题加以区分。
而儒学第三阶段的笔墨则完全集中在理学集团,随也提及事功学派中的叶适,但更多是把叶适当作政治立场接近的盟友看待,对事功学派中的陈亮却着墨不多,书中甚至有一段将其与皇帝近幸密切联系起来来分析其政治立场。可见作者在书中为了突出士大夫的“政治”这一属性,对他们之间在“文化”属性中的区别稍微简略了一些。在谈到理学集团看待“內圣”与“外王”之间关系时,作者认为建立形上世界的“內圣”之学在理学系统只处于第二序,而第一序仍是重建秩序的“外王”事业。这种说法却和理学集团的某些具体活动不相符合,二程、朱、张、陆对王安石的批评正是从其“內圣”不足展开的。他们也几乎都认为“外王”事业应该建立在“內圣”完善的基础上,可见他们在政治实践上认可的是以“內圣”为本,再去践行“外王”事业的。这种矛盾也是由于作者重“政治”的一个体现。三、材料分析与史学方法作者在自序中就提到这本书的创作原因,“在为德福文基金会的标点本《朱子文集》写一篇介绍性质的序文时,史料中所隐身出来的问题层出不穷,逼使我步步深入,改变了原来的写作方向。”由于作者一开始接触的资料便是《朱子文集》,所以本书的视角也就以朱熹为主,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在书中的观点往往借朱熹的观点加以发挥、扩充。
朱熹的著作、来往书信成为作者研究朱熹学术和政治取向的重要材料,其中所涉及人物和事件也使得作者进一步搜集相关资料,比如其他人给朱熹的答信、所涉人物的文集著作以及其它有关事件的记载。这样从材料来看,也是从朱熹为出发点,围绕着他的看法和交游来往延伸到和他同时期的人物和事件,再梳理历史前后的有关史料,一个朱熹的历史世界便形成了。作者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材料,通过细致地考证,不仅揭示了宋朝士大夫儒学发展的脉络渊源,也对宋朝政局变动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尤其是对孝、光、宁三朝间理学集团和官僚集团的政治斗争这一部分的论述,将“庆元党禁”这一事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原因揭露出来。由于整个论述过程结构庞大、所涉材料非常多,这里仅举“王淮罢政”一例来表现。作者通过周必大的《思陵录》,对周必大与王淮在高宗葬礼问题上争执进行解读,得出孝宗逐渐支持周必大而冷落王淮的结论,在其所记王淮罢相的详细过程中,提到许及之,薛叔似是以拾遗、补阙的职位攻去王淮的,而作者又根据楼钥《王公(淮)行状》中的记载得知正是官僚集团内部成员林粟向皇帝进言“增置遗、补”,而许、薛二人正是由孝宗御笔所定。而在《思陵录》中又有记载:“上又语予曰:前日林粟谏官文字,俟使人到了,次第理会。
”这里谏官必定指许、薛二人,可见此事孝宗是知会过周必大的。作者考证了许、薛二人此时的理学背景,再结合《思陵录》中提到周必大在许及之奏劾王淮的当晚便得到这一报告(此时周必大导灵至永思陵未返),可知孝宗与周必大对此必定早有安排。等孝宗“封薛叔似文字,付王左相,(王淮)遂入奏,乞罢政”。孝宗对此也毫不挽留,“止于一押而已”,可见孝宗想要罢免王淮之心早已有之。《宋史·孝宗纪》载:“帝既用薛叔似言,罢王淮,诏谕叔似等曰:‘卿等官以拾遗、补阙为名战国儒家思想为士大夫政治奠基,不任纠劾。今所奏乃类弹击,甚非设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更是坐实了作者的推论。最后,作者在分析孝宗与周必大罢免王淮为何如此大费周章时,作者又通过其它材料,看到了王淮执政期间,他与台谏早已互为表里了,而林粟的建议简直是给孝宗送来一个绝佳的机会。以上作者的一系列论述,足见其对材料认识之深刻,对考证运用之熟练,体现了高超的史学功力。作者在著作中还多次将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知识加以利用。整本书的主要内容在政治史和思想史之间反复切换,最终呈现出独具宋朝特色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作者可以说为中国古代政治史与思想史的互动作了一次完美的示范。在具体史学研究中,作者还别出心裁地使用了心理学知识来分析孝宗、光宗两位皇帝的思想动机。
作者借西方心理学中“自我”和“意我”来解释孝宗对高宗的复杂感情,也从借用“认同危机”和“心理挫折”等概念来还原孝宗的心理成长路程,并以此解释为何在高宗长期力主“安静”的情况下,孝宗内心依然保持着对“恢复”的渴望。作者还创造性地将孝宗“三年之丧”从心理上加以分析,认为这包含了孝宗内心怀着对高宗“未觉识的罪恶”,这种“罪恶”来源于孝宗内心对高宗的反抗、不满和怨恨。这种解释不可谓不大胆,却又让人耳目一新。总而言之,这本书从材料出发,详加考证,以朱熹为视角,以政治、文化为线索,以士大夫和皇权为考察对象,运用多种史学方法,对宋朝权力世界的现象进行说明,向读者展示了一个近在眼前的历史世界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