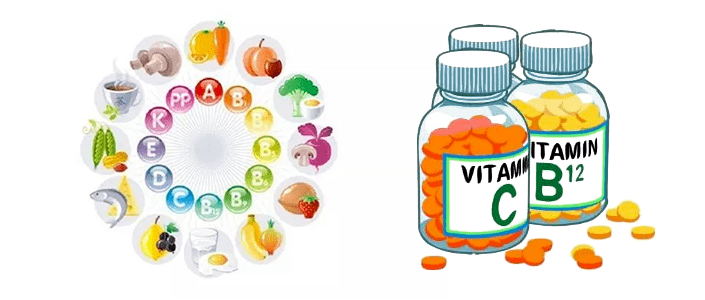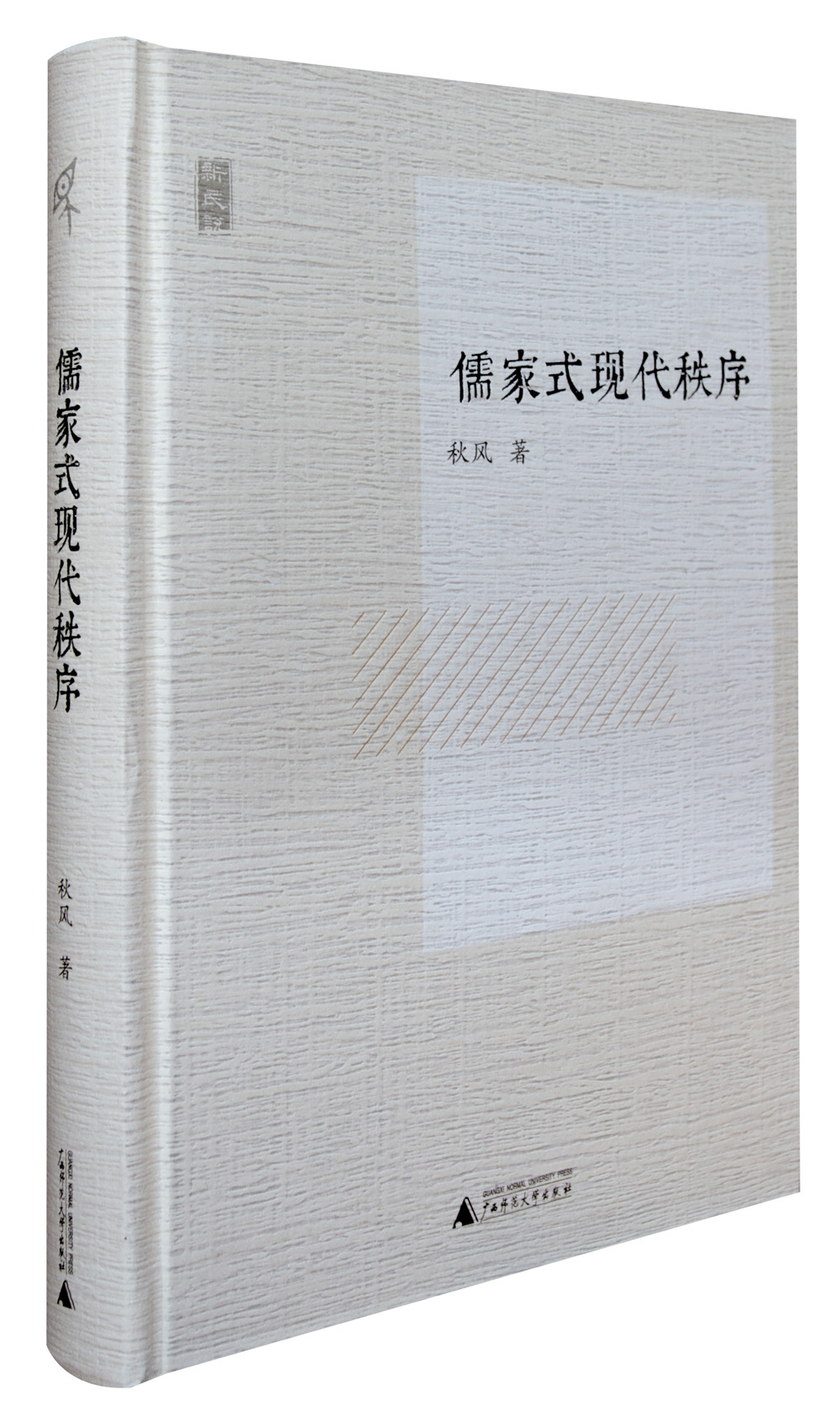当代儒学复兴的多元价值追求最终必须要归宗于孔子原创时代的价值论承诺
当代儒学复兴的多元价值追求最终必须要归宗于孔子原创时代的儒学价值论承诺,如此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儒学复兴”。而厘清孔子儒学的价值论承诺也是重建儒家哲学体系的必然要求,一个完整的儒家哲学体系必须要具有清晰的价值论承诺,而此价值论承诺又要有其真实的本体论支撑。孔子儒学的本体论依据是由“易道生生”给出的“生生”本体论,那么此“生生”本体论又给出了怎样的价值论承诺呢?其终极答案仍然要到《周易》哲学中寻找。
一、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价值宗旨
任何理论的产生都内含着一定的价值诉求,而这一价值诉求又反映着理论产生于其中的时代面貌与现实需求。不同时代的儒学虽然同宗于孔子儒学,必然具有本质相同的儒学宗旨,但由于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时代主题,面对着不同的时代境遇,又必然具有不同的价值诉求。当代儒学复兴之路中的多元价值诉求都代表了时代的一种声音,但在这种多元的价值诉求之上,我们还应当追问孔子儒学的终极价值追求是什么,追寻孔子儒学的终极价值论承诺,从而找到儒学的核心宗旨,使当代的儒学复兴找到终极的价值指向。这就要回溯儒学的发展历史,探索孔子儒学的价值论承诺是什么,而儒学史中最普遍公认的儒学价值诉求就是“内圣外王”。“内圣外王”早见于《庄子·天下篇》: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庄子·天下篇》为中国最早的学术思想史概述,由于“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导致了“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表明“内圣外王之道”本来是“天下大乱”之前中国学术的共同价值追求,贤圣之明,道德统一的价值追求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只是因为后来的“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造成“百家往而不反”,以至“道术将为天下裂”。既然“内圣外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诉求,而孔子本着“述而不作”的精神,编撰“六经”原典以传承传统文化,则此“内圣外王”的价值追求必然内含于“六经”原典之中。而“百家众技,不该不遍”,“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故诸子百家皆为“一曲之士”,“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不能传此“内圣外王之道”。故“内圣外王之道”就成为孔子儒学独传的价值追求,亦成为儒家区别于诸子百家的核心理念。此为孔子“述而不作”,以“六经”原典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意义所在。
但在“六经”原典与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之中,并没有对“内圣外王”的特别强调,“内圣外王”只是作为一条暗线贯穿于儒学思想体系之中。真正使“内圣外王”成为儒家经典话语的是宋明理学。宋明理学虽然在事实上对传统儒学进行了体系化的哲学建构,但在宋明诸儒的理论意识中却没有要刻意建构一套儒家哲学的思想体系,只是以“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的精神阐释儒学的思想,以应对佛老的挑战。故宋明诸儒的思想主要是以语录的形式,或注经解典的方式展开并流传的,而不是现代哲学理性表达意义上的专业化的系统理论阐释。故宋明理学在其理论自觉之中都是“注经”、“解经”,自认为忠实于孔子儒学思想的本意,而不是自己的独创或原创。而且宋明诸儒对儒家经典的理论价值没有任何怀疑,全部争论都在于如何理解经典的具体语意,及如何践行经典的具体要求。故宋明理学虽有气学、理学、心学之争,诸儒之间往来争辩亦多有不同,但都以如何实现儒家的“内圣外王”为同一宗旨,“内圣外王”成为宋明理学诸儒共同的价值追求,亦是儒家学派公认的共同价值诉求。
二、宋明理学对儒学宗旨的误读
宋明理学在其文化自觉性上突出了儒家思想对“内圣外王”的价值追求,以之区别于佛老出世的价值追求,而如何实现此“内圣外王”之道就成为宋明诸儒理论纷争的焦点。在北宋诸儒的理学构建之中,多以《易》为宗,“范仲淹泛通六经,尤长于《易》,欧阳修亦著《易童子问》,胡瑗以《诗》、《书》为文,长于《论语》、《春秋》之学,而于《易》尤精”,公认的理学鼻祖周敦颐更是以《周易》的太极阴阳理论创造出《太极图说》的宇宙生成论理论体系,张载也是根据《易传》形成其气化生生的哲学体系,程颐亦终生研《易》,留下《伊川易传》。程颢的“天理”二字虽说是“自家体贴出来”,但其理论来源则是《易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理论宗旨。“理、性、命”始终成为宋明理学论争的核心概念和范畴。张载言:“德不胜气,性命于气;惟胜其气,性命于德;穷理尽性,则性天德,命天理。”程颢言:“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又言“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程颐言:“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穷理尽性”即为“内圣”之途,“以至于命”即为“外王”之路,仍然是孔子儒学以《易》为宗的儒学思想进路,但其对《易》理的解读已不得孔子宗旨,从而对如何实现穷理尽性没有统一进路,以至分争不断,到朱熹则彻底改变以《易》为宗的儒学宗旨。
北宋诸儒以《易》为宗的思想进路到朱熹得一大变,由以《易》为宗变为以“四书”,尤以《大学》为宗。朱熹虽然著有《周易本义》,却认为《周易》本卜筮之书,故在其理学体系中并不以《周易》为重,而是着重阐发《大学》“格物致知”的理论宗旨,将《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列为“四书”,置于“五经”之前,使宋明理学从此开始以“四书”为宗,尤其以《大学》之道的“三纲领,八条目”为儒学绝对宗旨,影响了整个后世儒学的发展方向,具有极大的儒学思想史转向的学理意义。而《大学》与《中庸》都本来只是《礼记》中的篇章,只是儒学以《易》为宗之下的具体理论展开,并无超越于“五经”之上的学理地位。二程发明《大学》“格物致知”之说亦只是在解释如何实现《易经》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价值论承诺时而加以阐发的。因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给出的价值论承诺表达的必然是孔子“志于道”的终极价值诉求,是支撑儒学“内圣外王”之道的内在学理依据,完全是在“形而上者谓之道”的层面展开的,而其践行则必从“形而下者谓之器”做起,不能凌空蹈虚,故二程发明《大学》宗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是儒家思想吗,指点学者如何“下学而上达”。故《大学》是在“形而下”的层面言说“形而上”,在思想的层级上低于《易传》。就学理而言,孔子确定“六经”体系,而《易经》既然为“六经”之首,则《易》道自然贯通“六经”,而《大学》之道在学理上就是《易》道的具体展开,是指引学者进德修业的路径。而朱熹直接将《大学》提升为“四书”之首,又将“四书”作为“五经”之首,从而在学理依据上颠倒了“四书”与“五经”的主次位置,使儒学宗旨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朱熹评点《诗经》、《易经》与《春秋》说:
诗是隔一重两重说,易与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说。春秋义例,易爻象,虽是圣人立下,今说者用之各信己见。然于人伦大纲皆通,但未知曾得圣人当初本意否。且不如让渠如此说,且存取大意,得三纲、五常不至废坠足矣。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须理会经,先须于语、孟中专意看他,切不可忙;虚心观之,不须先自立见识,徐徐以诶之,莫立课程。
朱熹居然言欲得圣人本意,“未须理会经”,先须学习《论语》、《孟子》,却不知圣人本意皆源自“六经”,在致思的逻辑上应当是欲得圣人本意,先求之于“六经”之中,而以《论语》、《孟子》辅证之,而不是如朱熹一样的反其道而为之。虽然这只是一种儒学内部学理依据的主次颠倒,尚不至于彻底颠覆儒门宗旨,但在学术理路的具体价值追求之中已经不是“取乎法乎上”,而是“取法乎下”了,由《易》道的“形而上”进路落入《大学》之道的“形而下”进路。虽然《大学》之道在终极的价值指向上也是形而上的生生之道,但《大学》之道的整个理路只是统摄于《易》道之下的“下学而上达”的教化之道,而非直言性命之理、直达性命根源的终极之道。从而朱熹解读的《大学》之道就没有一个终极的学理依据,无法真正达于现实生命存在之道的自在与自为的统一。所以朱熹的理学总有勉强、造作的气质,缺少生命自在的自然、自由与圆融,并因此受到与其同时的心学代表人物陆九渊的批评。正因为朱熹不解《易》理,必然错解《大学》,并且对传统儒学的“理、性、命”等核心概念进行符合己意的曲解,亦由于错解“理、性、命”的概念内涵,从而造成其思想理论系统之中“理与气”的对立,“性与情”的对立,“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对立,“人心与道心”的对立,等等,使理学概念更加混乱,歧义频出,使儒学继续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轨道上行进,异化了孔子“述而不作”,求“性命之学”、“为己之学”的儒学宗旨,使后世理学日益僵化、教条化,最终异化成为“以理杀人”的封建理教。
而朱熹不但对《易》与《大学》及“四书”的学理地位进行了颠倒,还对古本《大学》进行了增改,不但改变了原文的章节次序,还增加了对“格物致知”的一段解释,以之符合自己对《大学》的理解。这就不仅是对《大学》解释的私加己意,而且篡改了原典,使后儒在“格物致知”的进路上聚讼不已,这是儒学发展史中的重大理论事件,亦是朱熹犯下的严重错误。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理学因朱熹而大昌,亦因朱熹而大错,在这一点上,亦可以说朱熹是理学的罪人,因为朱熹完全是在《易》理之外解释《大学》,故可以完全按一己之意解释,解释不通就认为原文阙简,又以己意篡改之。孔子言:“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朱熹显然缺少了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治学精神,过于自信而贻误后人不浅。孔子曾经慨叹:“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似乎预言了儒学后世的可能发展。王阳明早就否定过朱熹对古本《大学》的篡改,但只是在“亲民”与“新民”之争,及对“格物致知”的不同理解上争论,而没有在学理上解读古本《大学》如何具有逻辑完整性,及揭示朱熹的篡改存在的问题,故本文在此分辨之。考诸《大学》原文: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此节被认为是《大学》的经,全部《大学》宗旨已于此节表明,而其下各节只是分解此节经义的传。以《易》理一以贯之于《大学》,可对此节《大学》之道作如下解读:
“德”即《系辞传》言“日新之谓盛德”之“德”,而何以能日新?本于易道之“生生”,“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故生生而日新其德。“明德”即明晓此日新之盛德,“明明德”则是君子要将自己已经明晓的生生日新之盛德行之于天下国家,下文“八条目”只是言此生生日新之盛德自然展开之过程。而“亲民”则完全由此“明明德”而行之于天下国家之自然逻辑发生而来,生生日新之盛德行于天下国家,民与我皆为“生生”而来,自当本于“生生”而相亲。“明德”即为“内圣”,“明明德”则是“外王”之行,“亲民”则为“外王”之必然结果,故“亲民”本于“明明德”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是儒家思想吗,为“明明德”所内含;“外王”本于“内圣”,为“内圣”所内含。“至善”即超越于善恶对待之上的“纯善”,《系辞传》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道所言之善乃为继道而行之至善,此一阴一阳之道又本于“生生之谓易”,故此“至善”即为本于“生生”之“纯善”。“止于至善”即止于生生之道,以成“明明德”而“亲民”之事业,“止于至善”即内含于“内圣外王”之道中。故所谓“三纲领”可以“明明德”一语概之,故其下文只言由“明明德于天下”而展开的“八条目”,虽未明言“亲民”与“止于至善”,而二者已自在其中,因“三纲领”本是一事。
具体到“八条目”,由“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到“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一段,展开的是一系列前提追问,可以直接概述为“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诚其意”。“明明德”为君子行生生日新之德于天下,而君子欲明其已明之德于天下,必先诚我之意,因“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故诚为联接天道与人道的结点,唯诚可以使人道通天道,故诚即为“生生”,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至诚无息即生生不息。故诚意为明明德之本,诚意为《大学》修身之道的起点与核心,而不是朱熹所强调的格物致知。故古本《大学》在下文解经之中乃从“所谓诚其意者”开始,而无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朱熹误解原文而认为“诚意”以“致知”为前提,“致知”以“格物”为前提,从而认为传文缺少了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故以己意增添对“致知在格物”的解释。而这一解释完全违背了《大学》原意,甚至背离了《大学》宗旨,因《大学》之道以“诚意”为“明明德”之根本,而朱熹增加注解之后成为以“格物致知”为“明明德”之本,在理论上造成时人及后世儒者的纷争,在实践上对于《大学》修身之道的功夫论进路造成误导。明末的刘宗周亦以“诚意”为宗,但其学理依据则是由王阳明的“致良知”发展而来,其重心是“意”而不是“诚”,最终落在“意”之“独体”上,其言“良知原有依据处,即是意,故提起诚意而用致知功夫,庶几所知不至荡而无归也”。可见其对“诚意”的理解是落在“意”上,而不是落在“诚”上,完全是沿着理学的内在进路而来,而没有从《易》理的生生之道,天道的至诚无息来理解“诚意”何以为《大学》之道的根本。
那么,“八条目”中的“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又当作何解释呢?仍然应当以《易》为宗进行一以贯之的解读。既然已知诚意是《大学》修身之道的根本,则知“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已经不再是对诚意的前提追问,而是语意一转,提出对诚意的具体要求,即以诚意求知,再将诚意所求之知用来格物。那么,由诚意所求之知是何知呢?因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之道,即至诚无息也,生生也,故诚意所求之知为“生生”之知也,以此“生生”之知去“格物”,就是让万物之生生各得其所,草长莺飞,鸢飞鱼跃,万物“各正性命”。《乾彖》言:“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表达的正是此至诚无息的天道生生之意。诚意即为生生之“盛德”的发用流行,以诚意所得之生生之知去格物当代儒学复兴的多元价值追求最终必须要归宗于孔子原创时代的价值论承诺,即为“明明德于天下”,由“格物”所成之万物生生之景象即为“物格”。“物格”即为万物各得其所,各正性命,生生不息的自然存在状态。如果万物已经各得其所,生生不息,自然意味着知已经至,意已经诚,心已经正,身已经修,国已经治,天下已经平,否则不足以称“物格”。
故“格物”是去安顿万物之生生,是生命实践,而“物格”则是万物已尽其生生的状态,是对存在的描述,二者不可混同。“物格”已自然内具“知至、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之内涵,故由“物格”而至“天下平”并不是一个由低到高的修身过程,而万物各正性命之后的静态描述。考之《大学》文本,只有“致知在格物”,与“物格而后知至”二语,并无“格物致知”之说,“格物”并不是“致知”的前提,相反倒是“致知”是“格物”的前提,在“诚意”的前提下由“致知”而后去“格物”,由实践性之“格物”之行而达于描述性之“物格”之境,而自然“知至”以至“天下平”。故通常所理解之由“格物、致知”到“诚意、正心”,再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内圣外王”之道完全是在朱熹的错误理路上展开的理解,必然或流于空疏理论而不切实用,或落入僵化教条而成为某种绝对的道德律令与简单的道德训戒。王阳明曾以“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解释“致知在格物”,可以说与本文所述之意暗合,但其将“致知”解为“致良知”,又将“良知”仅仅理解为道德层面的“知善知恶是良知”,从而定义“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就使“形而上”的“生生”之明德层面的“致知在格物”变成了“形而下”层面的“知善知恶”、“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最终必然要落入与朱熹一样的道德教条或道德说教之中。
而朱熹之所以曲解《大学》,则因其不解《易》理,完全在《易》理之外解《大学》,如果不讲根据,仅仅依赖《大学》原文进行解释,自可随文赋义而任意曲解,当有义理不通而无法解释之时,就只能以错简或阙简责之,甚而不惜篡改原文,私加文本,以附己意。这种对经典的曲解造成的最大问题就是使理学失去了由《易经》哲学提供的“生生”本体论的支撑,仅仅以凌空蹈虚的一个“理”字无法真正支撑起理学的整个思想体系。因为“理是什么?”这本身还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怎么可能真正支撑起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呢?而由封建道德造成的“以理杀人”更是这一理学歧路的严重异化造成的恶果,以至招来现代启蒙思想的极端仇视,使鲁迅于中国历史中只看见“吃人”二字。而“吃人”与“生生”之道恰为对立,乃南辕北辙之别,却可能与“以理杀人”有某种联系,形成礼教吃人,故中国历史中的所谓吃人礼教在思想根源上乃是理学的异化,而非儒家文化本然如此。故今日儒学的使命乃是正本清源,回归儒家思想的生活本源,开新儒学,重建儒家哲学。
三、以《易》为宗的儒学价值论重建
任何哲学体系都必然内在承诺某种对人而言的价值,而此价值论承诺又必然以此哲学体系的本体论承诺为支撑。现代西方哲学拒斥本体论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造成其价值论迷失,一切固有哲学及新兴哲学体系的价值论承诺都失去了本体论根据,从而使整个社会都进入一种价值失范,“怎么都行”的混乱状态。海德格尔最后无望地说:“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留给我们的唯一可能是,在思想与诗歌中为上帝之出现做准备,或者为在落没中上帝之不出现做准备;我们瞻望着不出现的上帝而没落。”这是西方哲学的悲哀,自诩为“爱智”的哲学却无法解决人类“如何去存在”的问题,仍要乞灵于上帝的临在。“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这已经不是海德格尔奉献终生的存在论渴望,而是一种心灵无所归依的价值论乞求;上帝回答的不是“存在(者)何以存在”的存在论问题,而是“此在之人何以存在”的价值论问题。但尼采对“上帝死了”的宣判使海德格尔及所有西方人不得不“为在落没中上帝之不出现做准备”。这是西方哲学的更大悲哀,一种哲学理论无法给出可以安顿人类灵魂的价值论承诺,将人生的意义奉献给哲学领地之外的宗教与上帝,在本质的层面上暴露出西方哲学的无能。本体论的缺失已经注定了西方哲学的终结命运。
“生生”本体论作为一切哲学追问的终极,自在地赋予一切存在以“生生”的意义与价值。如果有上帝存在,那么上帝也只能在“生生”之中,一切价值与意义皆在“生生”之中,“生生”就是一切价值与意义的根源。人生的存在意义就应当是实现生生赋予的使命,故为“生命”,也就是中国哲学的“天命”,而此生生所命彰显在人之灵明自觉之中就被确认为人之本性,故此人之本性实乃生生之性,故《中庸》言“天命之谓性”。而此生生所命之性必然有其内在流行之理据当代儒学复兴的多元价值追求最终必须要归宗于孔子原创时代的价值论承诺,即宋儒所言的“天理”,此天理本质上就是生生之理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是儒家思想吗,所谓“天”,实乃是“生”,“天之理”即为“生之理”,从而人之生命存在的意义实现就是穷此生生之理,尽此生生之性,知此生生之命。故《周易》言“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正是对此价值论承诺的揭示。考之《说卦传》第一章言: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说卦”之义即解释卦“为何用”与“如何用”。“为何用”即为解释“卦”承诺了什么样的价值,为何目的而立;“如何用”则解释“卦”如何实现自己承诺的价值与目的。《说卦传》首章此段文字表明,《周易》之作是通过“生蓍”—“倚数”—“立卦”—“生爻”的方式,建立起一套阴阳变易的卦爻系统,并使这套系统“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最终达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目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即为《周易》哲学给出的价值论承诺。这也是任何人类性哲学都应当给出的价值论承诺,不能安顿人身心性命的哲学只能是无意义的精神浪费与思想垃圾。而价值论承诺的关键是其要有真实的本体论支撑,西方哲学由于找不到真正的本体而使其价值论承诺不得不求乞于上帝的存在,当上帝不在时必然是“怎么都行”的价值迷失与精神空虚。
儒家的《周易》哲学给出的“理、性、命”的价值论承诺以“生生”本体为支撑,“穷理”是穷“生生”之理,“尽性”是尽“生生”之性,“至命”是至“生生”之命。此“生生”之“理、性、命”是人生存在的终极根据,亦是人生所追求之“穷、尽、至”的终极目的。如此的人生就找到了安顿身心性命之所,不必乞灵于上帝或某种外在的存在。“理、性、命”皆在于我心之“觉解”(借用冯友兰语),此觉解又在于“生生”于我心之流行,故“生生”本体就在我之生命中,“性命”之“理”即“生生”,“生命”即由“生生”所“命”而来,故为“生命”。如此之生命就是与“生生”之道一体流通的存在,就是心有归依,身有所安的存在,不会如海德格尔所言:“现代人被连根拔起”。
而这样一条由“生生之道”贯穿其中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价值追求之路又如何可以达成,其内在理路如何呢?《说卦传》第二章续说八卦如何运用,指示着人之生命存在之“理、性、命”的实现进路。中国哲学的特质就是生命的学问,是可以应用于生命实践之中的“存在的学问”,也就是孔子所言的“为己之学”;而不是如西方哲学一样仅仅运行于思想之中的“思维的学问”,也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头脑中的风暴”,却与现实的生命存在无关。故而《说卦传》第二章言: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说卦传》首章言“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此章又言“将以顺性命之理”,其义一也,即利用《周易》的卦爻系统来指引和言说归属于人之生命的“道德”、“性命”、“理义”等哲学思想,但《周易》卦爻系统对此性命之道的言说方式却不是现代哲学理性化的逻辑推理与理论论证,而是通过卦爻系统内含的“象、数、理、义”来综合演示生生之道流行于万物之中的具体表现形态,完全是一种存在论的生存指引。卦爻系统完全就是对现实存在的抽象化图像演示,而不是思维之中的理论言说。故《说卦传》此章解释《周易》卦爻系统的建立分作三个步骤:首先是立天、地、人三道,即立天道为阴阳,立地道为柔刚,立人道为仁义。其次是阴阳爻互错而成六画之卦,即将天、地、人三才之道“两之”而“分阴分阳”(“一阴一阳之谓道”),成为每卦六爻之基本结构,从而形成由上卦与下卦组合而成的六爻重卦,实是对天道流行的图示化演绎。最后是在此“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天道基础上“迭用柔刚”,即以地道的刚柔变化叠加于天道的“一阴一阳”之上,演化出六十四卦的“生生”之理,形成以六十四种不同的“六位卦象”组合,演示出完整的《周易》哲学生命体系,即“六位而成章”。
由此可见,《周易》哲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价值论承诺可以贯通《中庸》的核心命题,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再引而申之,亦可将之与《大学》之道的“三纲领”,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相贯通。“天地之大德曰生”,“明德”即为明此生生之德而“穷理”,“明明德”即为将所穷之“生生”之理再明之于天下,而此明理于天下的过程即为“亲民”。而“亲民”不过是让天下人明“生生”之理,尽“生生”之性的过程,《中庸》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而天下至诚者,生生也。尽生生之性,则能尽人性、尽物性、赞化育、与天地参。故尽性方能“亲民”,因我与民同具“生生”之性,我才能得以亲之。“至善”即“天命”之生生之善,“止于至善”即为止于“生生”之所命,即为“以至于命”。故《周易》哲学贯通于《大学》与《中庸》之道,如此才可以成为“六经”之首,为孔子的“性与天道”之学,亦为孔子所求之“为己之学”。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