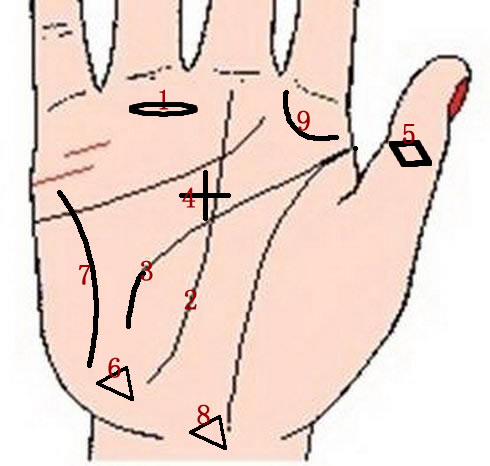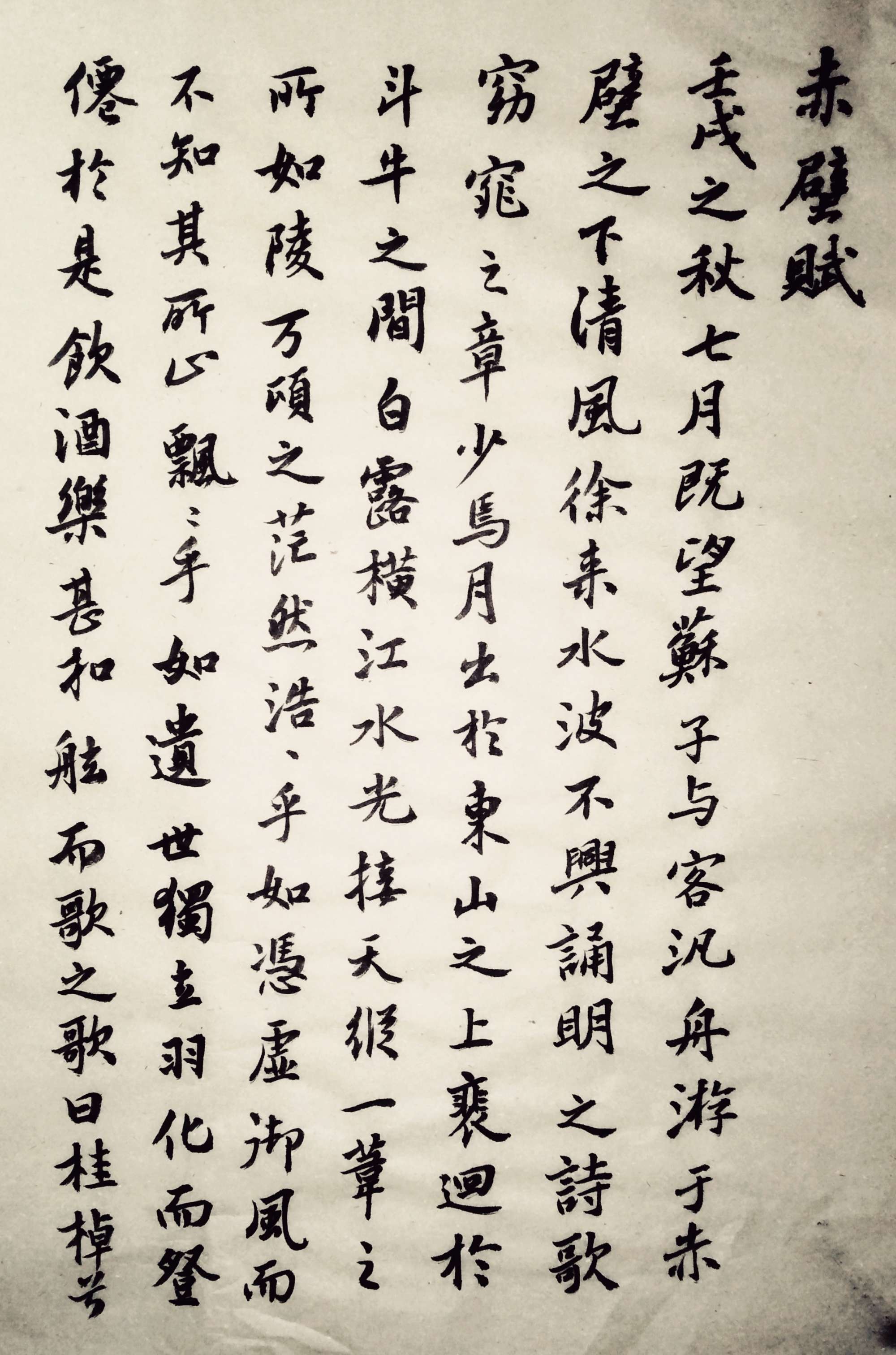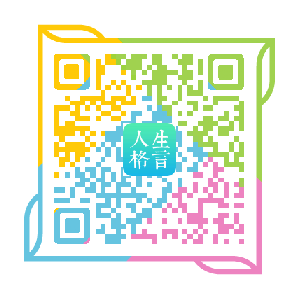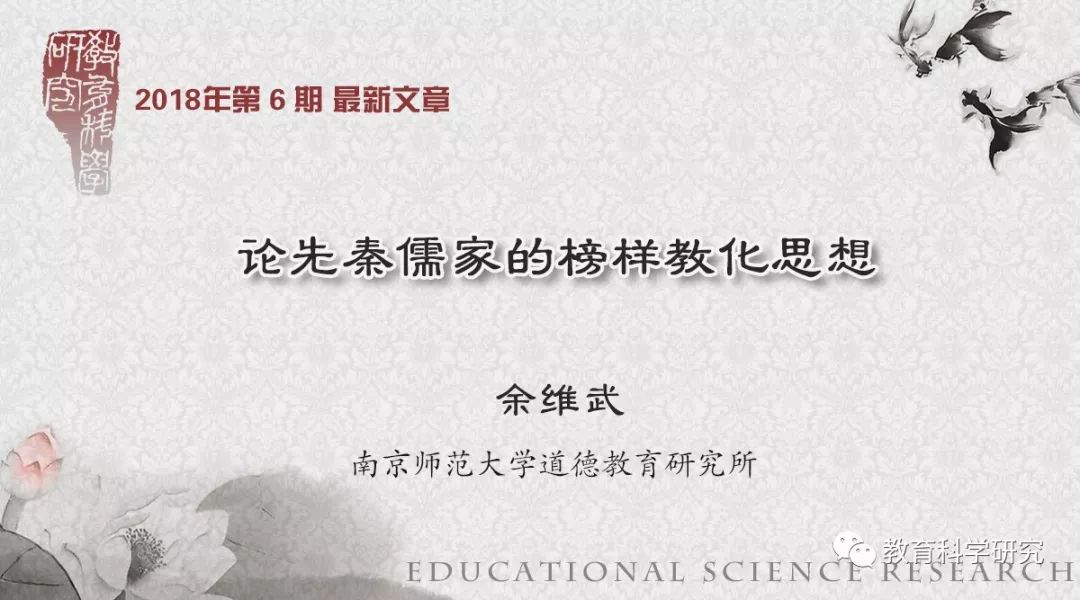
摘要
在先秦儒家的道德教育理论中,道德榜样占据着异乎寻常的关键地位。从其人性论假设与社会理想出发,先秦儒家不仅将树立道德榜样视为道德教育的最为有效的方法,而且将其视为社会控制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儒家人性论是先秦儒家榜样教育的理论基础;教师在先秦儒家的榜样教育思想中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礼则为先秦儒家的榜样教育提供了一个直观有效的途径。
关键词
先秦儒家;道德榜样;道德教育
在先秦儒家的道德教育理论中,道德榜样占据着异乎寻常的关键地位。对道德榜样在道德教育中巨大作用的深信不疑,在先秦儒家的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譬如,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孟子说:“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孟子·万章下》)荀子说:“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荀子·劝学篇》)这些言论都极大地肯定了道德榜样的社会教化作用。先秦儒家道德教育思想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假定之一是,道德上的榜样自然而然地吸引着人们。在先秦儒家的著作中可以经常看到这样的言论,譬如,孔子认为“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
一、儒家人性论——先秦儒家榜样教育的理论基础
先秦儒家之所以如此重视并高度评价道德榜样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与其人性论假设密切相关。
先秦儒家的人性论假设是:不管是性善性恶,人天生具有向善的可能和欲求,都可受君子圣人教化或通过自我修养而达到自我完善。
孔子对于人性的说法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即人生来具有相近本性,这种相近的本性由于后天影响而变得不相同。但是,相近之性是善是恶儒家思想是谁提出,孔子并没有直接阐述明白,故有人认为孔子主张性无善无恶。然而,如果联系孔子的一贯思想及其多方面的论述,他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人性本善的观点。
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以“仁”为核心。“仁”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概而言之,从内容上讲,“仁”的基本含义即“爱人”或“泛爱众”;从方法上讲,“仁”所包含的忠恕之道(推己及人)是一种行仁之方。而要推己及人则必须包含一个前提,即人同此心,心同此欲,由此才可能“能近取譬”,将心比心。可见,孔子的“性相近”中包含着人有着普遍相近本性的思想。“爱人”的原则通过忠恕之道或推己及人的行仁之方而得以实现。从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以及由此实现的“爱人”原则来看,孔子的“仁”实际上包含了人皆有“爱人”道德属性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观点。同时,仁爱从“孝悌”推出来,即人以“仁”为本,而“仁”又以“孝悌”为本,而“孝悌”在孔子看来,是一种由天然血亲之爱为本始的“天赋德性”,天然亲情是一切人际关系的原点,父子手足的人伦道德源之于天然血亲的感情。由此可见,孔子不但认为人之为人的本质在于人伦道德,而且也间接表达了人的这种德性属性是先天就存在的。[1]这样,基于血缘亲子之爱上的仁爱之心,以及“忠恕”之道中含有的推己及人的普遍道德能力,就为人接受教化而向善提供了可能性。同样,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道德教育的可能性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孟子在孔子“仁爱”之心的基础上作了发挥。孟子认为,人之性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这就是人所特有的仁、义、礼、智四种道德心理情感,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所以,“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下》)。孟子把“人性”特指为道德心理情感,而这四种道德心理情感为人先天具有,即“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正因为“善端”“四心”本在于人心之中,所以只要使之扩而充之,就可成为仁、义、礼、智四德。从人性具有善端的前提出发,孟子认为“尧舜与我同耳”,故存在着“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可能。但人具有先天善性并不等于人的所有天生本能生来都善,后天环境浸染加上主观不努力,就会使人丧失善性。可见,人善与不善,有后天人为在其中,有人为不善,“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善乎?”(《孟子·告子上》)这一点也体现了孟子重后天教育与修养的思想。
与孔孟相反,荀子论证道德教育的可能性则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首先先秦儒家的道德教育理论中的道德榜样教育的理论基础,荀子认为,正因为人性为恶而缺乏善,故产生了为善的需要,“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苟有之中者必不及于外。用此观之,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荀子·性恶篇》)。因为,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同上),人类就不可能生存先秦儒家的道德教育理论中的道德榜样教育的理论基础,故人有为善的必要。其次,人性虽恶,但人性中存在着能够知善的能力。荀子认为:“途之人可以为禹,遏谓也?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则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同上)“理”指仁义法正可以被认识和把握的根据,“质”和“具”是存在于人自身的可以认识和把握仁义法正的素质与条件,实指人的理性能力。因此,人人都具有“可学而能,可事而成”即“化性起伪”的能力,也就是说,人人都有可以成为圣人君子的可能。[2]因此,荀子又认为“凡以知,人之性也”(《荀子·解蔽》),把人对于仁义道德具有“可以知”“可以能”的“质”“具”作为人性的规定。正因为人具有对善的需求和“可以知”“可以能”的认识能力,所以人可以通过接受教师的教导,积善成德,化性起伪,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乃至成为禹一样的圣人。
正因为人性无论是善是恶均欲求向善,故道德高尚的仁人君子对欲求向善的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一个人道德越是高尚,他对学习者的吸引力就越是强大,而道德完美的圣人则具有神奇的道德力量,散发出巨大的道德感染力,能够在情感上打动每一个人,吸引每一个人向他学习而进行道德践履。因此,从人性论假设出发,在道德教育中,先秦儒家把道德榜样的作用放在了异常重要的位置上。他们认为,由于人天生具有学习道德榜样的能力与欲望,这种学习可能是对周围人的无意识的仿效,因此,善择邻人(生活环境)就显得很重要(如,“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学习更可能是自觉地试图仿效教师或者君子贤人的态度与行为。尽管个人可能受到坏榜样的影响,但多数人必定为道德榜样所吸引并自觉仿效,“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二、教师在榜样教育中的关键作用
在先秦儒家的榜样教育思想中,教师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
先秦儒家的教师观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一方面,从最广泛的意义说,一切能够促进、帮助自己的德行得到改善的人都可称为教师。故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另一方面,就狭义来说,只有善于学习,深刻地把握先王之道、仁义礼乐的道德精神的君子贤人才能够担任道德教师,即“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先秦儒家深信,先王之道,仁义礼乐的道德精神蕴涵在古代圣贤流传下来的经典中,只有道德学问精深的君子贤人才能够领悟到蕴涵在经典中的先王之道。所以荀子说:“况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非顺孰修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荀子·荣辱》)由于只有修养精深的君子才能把握先王之道,故此,“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荀子·致士》)。只有道德学问精深的君子才能具备充当教师的资格。
对于先秦儒家来说,教师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言传,向学生传授蕴涵在《诗》《书》《礼》《乐》等文化典籍中的道德规范、道德精神;二是通过身教,以自身的道德行为、道德人格为学生树立起一个可供仿效的榜样;三是帮助学生鉴别、选择那些道德上足供效法的榜样(现实中和历史上的)。
先秦儒家提出的修身,不是指个人只能依靠自身努力。自身努力和教师的教诲都是必要的。孟子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孟子·万章上》)每一个道德高尚的先知先觉者都可以并且应该自觉成为后知后觉者的老师。从时间的维度上,教师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现实中的教师,另一种是古代圣贤。对于先秦儒家来说,在可供效法的意义上,古代圣贤具有教师的意义,故荀子说:“故学者以圣王为师。”(《荀子·解蔽》)道德修身就要学习记载圣王行为与精神的著作。而教师或者其他活着的贤人则是现实中在道德上足以效法的人。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论语·里仁》)因此,教师的作用固然体现在向下一代传授道德知识上,但最关键的是体现在作为一个具有道德学问的君子贤人而成为可供学生学习的榜样。
从人性论假设出发,先秦儒家关于道德榜样教育有两个重要假定:第一个假定是人们通过仿效道德榜样来进行道德学习,向人们引荐道德榜样是反复向人灌输某种道德行为准则的最好办法。因此,在先秦儒家著作中,道德教育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教师不仅要以自己的高尚品德作为学生的榜样,而且要发现教育学生的道德榜样。与之相反的是,帮助学生辨别那些不宜效法的人——道德榜样的对立面。正因为仿效道德榜样在先秦儒家道德教育中是如此重要,所以,如何认清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的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能力称之为“知人”,即:“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论语·颜渊》)故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因此,教师的另一个作用是帮助学生鉴别他人(现实中的与历史上的)的道德品质,以选取那些在道德上足供效法的人。在《论语》中,常可以看到孔子如何指导弟子们品评历史与现实中的人物的道德品质,从而帮助他们选择可供效法的道德榜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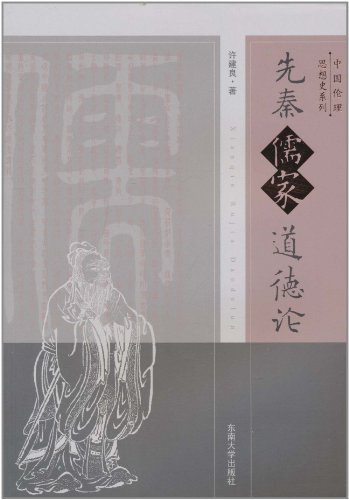
先秦儒家关于道德榜样的第二个假定是:人们通过仿效道德榜样而认识道德真理。先秦儒家确信,道德高尚的教师或贤人君子体现着圣人之道,是礼义道德的具体化身。人们向教师或贤人君子学习,就可能把握到圣人之道,养成高尚品德。荀子云:“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知其师也。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圣人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荀子·修身》)人们如果要养成高尚的道德,就必须效法老师。“故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则必为乱;察则必为怪;辨则必为诞。人有师有法而知,则速通;勇则速成……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荀子·儒效》)
三、榜样教育的有效途径——习礼
道德榜样之所以在先秦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除了基于儒家的人性论假设之外,还与礼在先秦儒家道德体系中的地位以及礼在道德生活中的作用有关,可以说,礼为先秦儒家的榜样教育提供了一个直观有效的途径。
关于礼应该注意两点:首先,礼的实践涉及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场合;1其次,礼和仁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礼的实践是仁的养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仁是人之为人的最高的美德。所以,先秦儒家假设一个人不通过礼的实践就不可能获得高尚的道德品质。
然而,礼的这些因素本身并不能解释合乎礼的实践就是一种美德,而不仅仅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得体优雅的举止。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考虑礼的第二个维度。对于礼的实践而言,紧要之处在于:人不仅要服从礼的要求,而且恰恰是要通过这种服从来表现自己,因此礼并非强加给人的,而是被人完全变成了自己的。荀子说:“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荀子·修身》)情感得到安静,既是说它们的和谐,也是说它们得到了充分的外在表达。通过礼,一个人内在的道德情感与外在的身体表达之间的间隙被弥合了。
如果礼应作此理解,那么礼之于仁——人的品德的不可或缺也就不足为奇了。儒家谈到仁有五种实践: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像其他道德实践一样,这些实践方式均需要借助礼:“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离开了礼,内在道德情感和外在身体表达之间所构成的整体统一性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样一来,正是在礼之中,而且是通过礼,个人在特殊的社会道德交往与实践中才作出了充分而恰当的反应、并且将其反应的性质传达给他人的道德意向才得到了展示。因而,并非离开了礼的实践就不能拥有仁,而应该说,离开了礼的实践,个人就不可能真正拥有任何美德。因为,具有完美德行的人,一定是一个能够把其内在的道德思想情感与其外在的身体表达融为一体的人。礼是个人完善的过程,这种完善表现为一种养成的性情、一种态度、一种姿势、一种特征、一种身份。礼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道德话语,一个人通过它从品质上将他自己确立起来,显示为一个独特的个体,一个完整的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

正是由于先秦儒家要求“仁”这种内在道德情感需要外显的礼的行为的完美体现,正是由于礼在道德生活中的这种重要地位,才为先秦儒家将榜样学习作为道德教育最为有效的方法提供了可能。礼毕竟需要人的身体的恰到好处的表达,礼和人的身体的这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在“礼”与“体”的同源上(繁体),而这就为道德学习者提供了具体可感的、有效的仿效途径。道德学习者可以通过仿效教师或君子的外显的道德行为(合乎礼的行为),进而体会到内含在外显的行为中的“仁”的道德情感,并最终把外显的礼的行为和内在的仁的道德情感统一起来,最终成为像道德榜样那样达到仁礼和谐的、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实际上,先秦儒家中所谓的“学”不仅应包括理智和道德的成长而且也应包括人身体的成长。身体的成长是儒家学习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以至于后儒把孔孟之道称为“身心之教”。确实,作为儒家教育范围的六艺,其中的每一项都要求人的整个身体的参与。虽然只有射、御是人的身体的操练,但礼和乐也要求身体活动的协调与和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秦儒家把自我修养的过程称为“修身”,是一个“体道”的过程。[3]
先秦儒家认为,不仅可以通过讲授文化典籍、讲解道德精神和道德原则直接传授道德知识,即所谓“言传”,1而且可以通过“身教”来直接予以道德示范。而教师则是礼义道德的具体化身,“礼”这种人伦道德交往的道德仪式,恰好是可以由娴熟地掌握了礼的教师通过示范来授予的,相传孔子即带领弟子习礼。“教”,《说文解字》解为“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表达的正是一种示范的教。这也正是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被称为礼教的原因。
总之,先秦儒家的榜样教育思想可概括如下:榜样学习的主要对象是教师,这里的教师是广义上的教师,既包括现实中的教师,也包括历史上的圣贤,或者说,一切道德高尚的人都可充当他人效法的教师;先秦儒家关于人性的假设为道德教育的榜样法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先秦儒家主张人的道德情感必须通过外显的礼的行为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又为人学习道德榜样提供了具体可感、切实可行的途径。对于先秦儒家来说,教师的最高境界是身教重于言教,行不言之教。最高明的教师,也就是道德最为高尚的人,其言行举止无一不散发出巨大的人格感染力,对学生犹如“时雨者化”,具有一种吸引人情不自禁地加以仿效学习的神秘的魔力。例如,颜回对孔子的巨大的道德人格魅力感叹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儒家思想是谁提出,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论语·子罕》)
四、对先秦儒家榜样教育思想的评价
先秦儒家无疑深刻认识到了道德榜样在道德教育中所具有的巨大作用,其道德榜样教育思想也给今天的道德教育提供了许多启示,例如,认为教师不仅要以自己的高尚品德作为学生的榜样,而且要发现教育年轻人的道德榜样,并且帮助学生辨别那些不宜效法的人——道德榜样的对立面。但是,笔者认为,如要深刻理解先秦儒家的道德榜样教育思想,就得首先从认识先秦儒家的理想社会模式开始。
先秦儒家的一个基本假定是,教育是改变人类行为的关键,因此教育也是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关键。其理想社会模式是,由道德上成熟的人来治理万民,从而形成一个道德成熟的社会。君子贤人通过先修己身,率先垂范,示教万民,万民则以圣王为楷模,受其教化,这也就是所谓圣人“神道设教”。而从其人性论假设出发,每一个诚心向善的人都会竭诚仿效道德高尚的圣人君子。2所以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通过这个途径,一个道德成熟的,稳定、强大、繁荣昌盛的社会将最终建立起来。

因此,从其人性论假设与社会理想出发,先秦儒家不仅把树立可供人效法的道德榜样视为道德教育最为有效的方法,且把它视为社会控制最为有效的办法。对于先秦儒家来说,有不同层次的榜样,乡有乡的榜样,国有国的榜样,天下有天下的榜样;有体现不同道德品质的榜样;有现实中的榜样,也有历史上的榜样。树立各种榜样与让人学习榜样儒家思想是谁提出,可以造就一个道德美好的社会。这种方法一直沿用到当代中国。对于道德榜样这种近乎神奇的影响与作用,今人称之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在道德教育中,道德榜样确实具有一定的作用,这种作用为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所证实,例如班杜拉的社会学习法。但需要指出的是,先秦儒家的道德榜样教育思想源于一个理想化信念:即人性的潜在道德感的同一性,并且进一步将之拟想为行为过程的合目的性的同一性,也就是在逻辑上把“应当是”转换为“正是”,并形成“榜样说”。因此,当把个人修身养性的结果由功能的有限性(自身)转向功能的无限性(仁政和社会道德完善)时,则不那么令人信服。因为,道德修养的理想主义在个人身上可以完成与现实的内在联结,而不可能实现与整个社会的现实联结。要实现这个联结,必须有一个前提:社会上的每一个个体都在意志上真正服从于体现人的本质同一性的善良意志,并在价值选择上最大限度地向往于同一的道德境界(追随圣人)。[4]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价值多元的时代尤其如此。由此所造成的弊端是,不是由于塑造完美的道德榜样而导致道德榜样失去可信性或者失去可仿效性,从而导致榜样教育流于形式;就是由于道德学习者被迫在外在言行上与榜样保持一致,而在内心情感认识上并不认同,从而导致道德学习者的人格分裂与虚伪。先秦儒家榜样说的另一个缺陷是,当把向道德榜样学习视为道德教育最为有效的方法时,存在着容易导致盲从的危险。因为,既然君子圣人是礼义道德的具体的、完美的体现,那么,一个人只要在言行情感上向君子圣人看齐就可以养成同样的德性,即“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庄子·田子方》),反省也仅限于省察自己的言行情感是否与道德榜样、与君子圣人保持一致,孟子对这种对于圣人或者道德榜样的追随与仿效作了最通俗的说明:“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孟子·告子下》)这无疑很容易导致在道德行为上对权威的盲从。这种对于道德权威、道德榜样的失去理性反思的盲从,有时会导致个人与社会的巨大悲剧。
先秦儒家的道德榜样教育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我国封建社会的道德教育中,而且明显地体现在1949年以后的道德教育中。例如,强调榜样的完美高大;从历史到现实,从学校到社会的各个系统,建立起完备周密的道德榜样网络。然而,正如前文分析所指出的,我们在学习、借鉴儒家的道德榜样教育思想时,要清醒地意识到其理论假设的缺陷。
[注释]
[1] 葛晨虹.德性与教化——儒家德性思想研究[M].北京:同心出版社,1998:94.
[2] 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53.
[3] 杜维明.人性与自我修养[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39.
[4] 陈少峰.中国伦理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导言17.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