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本文作者霍韬晦先生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讲师、香港佛教法住学会会长。已出版的著作或翻译作品有《佛教的现代智慧》、《佛家逻辑研究》、安慧《三十唯识释》原典译注、佛学《教科书》、《绝对与圆融》、《欧美佛学研究小史》等。本文原载《佛教的现代智慧》,本刊转载时略有删节。
何为佛教的现代智慧
我这里所谓佛教的现代智慧,意思是在佛家的哲理中,对现代人所面对的问题能有启发、对治意义的智慧。佛教的智慧,依我看来是有其普遍性的,故应恒常地起作用。我们今天即试图将其功能提发出来,以助解化现代人所面对的问题。
但是现代人所面对的问题很多:政治、经济、科技、社会结构、艺术潮流,各方面都发生问题。佛教的智慧,是不是都能给予启发呢?当然,佛教的直接贡献,不会是在科学技术或政治经济的内容上。虽然佛经中常常提到:“菩萨求法,当于五明处求”。五明者:一、声明,明语言文字;二、因明,明辩论逻辑;三、工巧明,明工艺技术;四、医方明,明医理药学;五、内明,明宗教哲学。据此,似乎佛教亦处理政治经济与科学技术的问题。原始佛教经典(如《善生经》)也谈及生产道德与节约消费的问题。如言家庭收支要有计划,其收入应分为四份:一作饮食,一作田业,一作积蓄,一作生利息。这可说是经济方面的事。政治方面,佛教赞成行议会政治,僧团内部亦行民主,一切财物全体拥有,公平利用。有事情时,要求所有出家人都参加会议(即“羯磨”,Karma,会议的主席称之为羯磨师);如是,僧团即构成一自治单位。这可说是议会政治的雏型。诚如上述,佛教亦接触到政治经济上的问题,其所提出的“转轮圣王”,即成为人君的典范。亦有人认为:佛教的经济观点,可以对治今日鼓励消费的“富裕经济”(),因为大量消费不一定好。这的确是一种启发。不过,若要把这些观念应用于现代,我想还是不够的。一来在训练方面,古老的佛教未可与现代人相比。二来佛教并未将科学技术与政治经济的发展视为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它涉及这些,是因为现实人生涉及这些,不能抽空而谈菩萨道。然而,佛教却看到人生方向不尽在此,它知道科技政经的方向有其限度,人生不能以此自足。佛教的智慧乃对科技政经发展趋势的反省,对其限度的批判,以替人生另寻起点,亦即替人生另寻终点。“世间善”是现实世间应有之善,故科学技术与政治经济的学问应该有,但此善有其限度佛家的智慧是什么意思,不能顺之而趋,以此善为终极,终极之善在“出世间善”,这是对现实人生的一种提升,人生由现实层而提升到理想境界。“出世间”的意思只是要转化现实人生,而非解作离开这个世界到别的世界去。《六祖坛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犹如觅兔角。”就是这个意思。
由此可知,如果说佛教有现代智慧,它的智慧不会在解决科学技术与政治经济的具体问题上。它不具备这些训练,亦不累积这方面的知识。说到这里,我想对知识和智慧这一对名词稍作解释,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佛教的贡献。
所谓知识,依我的意思,是对客观世界的了解。它是具体的、综合的;它以经验的摄收始,而以理性的整合终。它检核的标准在外,所以它是可以累积的、修正的。求知者本身并无意见,他只是顺势而趋。今天的科学知识即代表了这一方面。智慧,则并非为了说明个别的现象,亦不是要对具体的问题作分析或综合。它是非累积的,虽然从某一意义上说,智慧有继承,有开发,或亦可说是累积。但这只证明智慧有其普遍性。智慧代表人对他自己的各种活动的反省,由此而透出的一种慧识、一种洞见,使人自知其活动的意义,一方面又能超出其活动以达成人生更高的价值。这种价值的升进,即靠智慧推动、靠智慧选取,而智慧是由反省得来:一切宗教,一切哲学都有反省意味。由此我们区分知识与智慧:知识内在于每一知识领域内,智慧则超临于知识世界之上,俯视其发展方向以提点之,随时作出新的启发。
下面我们将佛教的智慧试作内容上的说明。这里拟提出四点:一、原始佛教的“如实观”的智慧;二、由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对无明烦恼的深层体验的智慧,及相应于此而成立的实践的智慧;三、大乘佛教说“空”的智慧;四、中国佛教说“判教”的智慧。
“如实观”之智慧
“如实观”是原始佛教的核心观念,意思是对事物能有一如其所如的把握。为了把握事物原来样子,我们要放下主观的认知条件。这些主观条件包括我们个人所受的教育和训练,亦包括我们处理事物时所选取的角度。我们透过自己的观点去看事物,事物便染上了我们主观的色彩。再由此推概,成一理论,或一系统。但结果结构愈严,所排斥者愈多,主观的壁障愈厚,距离客观的真实愈远。
佛教说如实观,有其历史背景。佛陀时代是一思想开放的时代,婆罗门教《奥义书》所说的“梵我一如”的思想已经解体。当时有很多思想家出来立说,各示其胜义,佛经上所谓六师外道、六十二见等。但从佛教的立场看来,他们对宇宙人生之讨论都出于主观构想,皆堕于“见网”(-jāla)。见网者,即一套套说法之网,每一思想家各提出一套说法,皆自以为见真理。但真理之所以为真理,应是客观普遍的,而不应彼此有异,彼此相对。故佛陀谓其皆不能如实,因皆不能去除主观条件的影响。而更重要的是,有些问题根本不能化为概念上的讨论。佛经记载当时思想界中有很多争论,如争论世界是否永恒?世界是不是无限大?理想人格终不终?命与身异不异?等等。
佛陀从来不参加这类问题的讨论。在有名的《箭喻经》中,一个婆罗门问佛陀何以不谈这类问题?佛陀以中箭为喻,说争论这类问题,就如一个人身中毒箭不先就医,而只寻问此箭从何射来?谁人射来?弓是什么造的?弦是什么做的?这些问题未及解决,其人已毒发身死了。佛陀的譬喻是很真切的,因为那些问题都无关于我们当下痛苦的生命。生命之痛苦是一真实的、存在的经验,不应化为形而上的理论。以一套套形上理论来套解生命的真实,有如瞎子摸象。所以佛陀说,这类问题都是“非义相应,非法相应”,“不趋智、不趋觉、不趋涅槃”,我们应该与真实之生命相应,如实知生命之苦,亦如实解生命之苦,故非如实观之不可。得如实观,亦即得“法眼”(即见“法”之眼)。在原始佛教之概念中,“法”与“实”同一外延。法即实,实即法,知法即知实,知实即知法。这是外延地说。内容地说,则法是实的存在状态,即所谓缘起状态,一切法均依缘而生、依缘而转、依缘而灭。所以说“见法即见缘起,见缘起即见法”,这是原始佛教对事物存在的一个看法,代表原始佛教的洞见。
原始佛教为了表示“缘起法”的建立是如实的,所以特重这种观法所获得的效果。要判分何者所见为实,何者所见为不实,便不能不有一检证的标准,此标准佛教即从实践上说明。佛经记载佛陀在未得正觉以前,即未得如实智以前,曾从印度传统之修行方法,先修禅定,不得果;弃之改修苦行,苦行六年,亦不得果,故知两者之不足。其不足之处,即在对客观之真实把握不着,把握不着即证明其观尚有虚妄,或尚由妄心所生。盖此观若是正确的,必能引生正确之行;由正确之行,必能引生有效之果。由此可知,佛教之“如实观”有效用上的支持。这种智慧与行动、效用的连锁结构,在今日而言,可谓极具时代意义。美国哲学,即特重知识与效用的关连,而以效用检验知识,则佛教重实践之教,可谓万古常新。所不同者,佛教言真理,并非只是将之看作使人生受益的设准。照佛教立场看来,实用主义者的讲法,有颠倒本末之嫌,因为它的最后裁决在人的经验生活。倘若人的经验生活能自我完成,又为何会有种种冲突、相对相害呢?所以此中必有一客观之真实在,人只有与之相应才能去除自己的“成心”。佛陀以“四谛”教人,第一谛是“苦谛”,目的即是要我们实感此人生乃一无常流转之存在,无常即苦。此只须一念直感即得,而不必更以种种抽象概念与思维,来作曲折的表达。《箭喻经》的精神即在此。
由此看来,近代哲学家、科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解析人生问题,往往对人生之存在感受不深佛家的智慧是什么意思,便急于罗列知识概念和专门术语以成一系统的做法,在第一步上可能已错了。这样做无异使人冒过存在之实感而归向知识概念。结果势必只形成各个解释系统,而互争高下。人心之粗动,一发不可止。此所以佛陀于中沉默也。
对深层烦恼体认之智慧及相应成立之实践之智慧
释迦以其真实之体验、真实之要求,成就其“如实观”;亦希望闻其教者,同样得“如实观”。就现实人生而言,人何以不得此“如实观”?人何以常陷于妄见之中?由此问题之追问,我们即可发现人的现实生命中有烦恼、有无明。人最大的无明,是对自我的执着(我执)。在自我观念的影响之下,只知实现自己的欲望,而排斥他人,于是一切“毒”、“盖”、“结”、“暴流”(皆烦恼之异名),都相沿而至了。所以原始佛教所全力对治的,主要是我执,到部派佛教和大乘唯识宗时才有进一步的分解。例如说,这些烦恼,自其存在的性质上看,又可分为分别性的烦恼和俱生性的烦恼两类。分别性的烦恼是在经验的层面上活动的,当如实智起,初次证见真实,便可以消散。俱生性的烦恼则是潜隐性的,它不与经验心灵之活动相应;它存在于有情生命的底层中,而与之一起翻滚。在一般情形下佛家的智慧是什么意思,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正如《胜鬘经》所谓“无明住地,虽得阿罗汉、辟支佛智仍不能断”。这是因为阿罗汉、辟支佛的智慧仍未“究竟”(透彻),对它们的存在“不知不觉”,所以对修行者而言,只要“无明住地”尚在,即可以由此再生起一切“心上烦恼、止上烦恼、观上烦恼、禅上烦恼、正觉上烦恼、方便上烦恼、智上烦恼、果上烦恼……”等像恒河沙数般多的烦恼。只有到达真正成佛的阶段,才可以全部断除,由此可见“无明住地”之深。所以人生之对治修行之活动,亦必须历劫多世,并非单靠概念知识,或只从理上看透,便能化解的。这是整个现实生命结构的事,必须步步实践才能步步转化及提升其生命之形态,绝不能掉以轻心。这就是佛教讲修行必须历无量世之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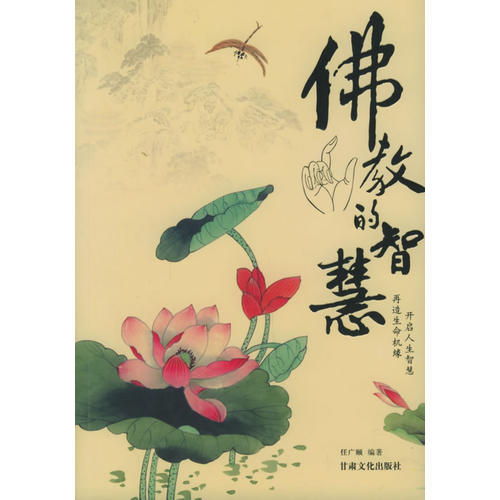
烦恼由浅而深有层层“住地”,则相应地转化烦恼之智慧亦有层层之序列。以智来对治烦恼,这是佛家说教的特色。烦恼有不同的分类,则智慧的分类亦有不同。以佛陀的广大的慈悲与愿力,既说法以度众生,则必不能以部分之众生为限,而必广及一切自我封闭、亦即尚有无明及烦恼之众生。于是,佛即以种种教化智慧,以说种种法,来分别对应于不同根机之众生,亦即各有不同之无明住地之众生,使之皆能从其无明妄执中上拔而出。沿此了解,则佛陀必有种种“方便智”之运用,以种种语言分别化解不同之众生之执。如是,即有《法华经》所说的实智与权智的观念出现。而权智者,即成佛后之智慧。在唯识宗,亦称之为后得智,以与成佛证真之无分别智(即如实智)分开。或在般若宗,则以此智具有指示众生以种种不同之解脱道之功用,故又名之曰道种智,以至一切种智。从另一方面看,原始佛教、部派佛教所向往的阿罗汉位格,由于缺此救度众生之智慧,即证明了他们的智慧不足;智慧不足即表示尚有无明,故《胜鬘经》说他们虽能出轮回,尽“分段死”,但尚有无明住地。天台宗即承此意说只有在兼断界外之无明之后,才能得佛智。
如上所说,一方面是烦恼的层层深入,一方面是智慧的步步透出。烦恼所在之处,即为智慧对治之处。这显示了烦恼和智慧的关系:智慧随着烦恼的体验而深化。小乘体验得较浅,大乘体验得较深。这种对烦恼体验的智慧,我想对现代人有极大的启发。现代人最大的问题,可能在于对自己的心灵、生命、及价值取向缺乏反省,或对自己的思想与行为过分自信,而从未想到此中亦有无明或烦恼在。现代人要闯过的第一关,是知识上的封闭。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各知识领域独立发展,平头排开,于是各据一义而推广至极,终而互相抵触。人不能兼取多个观点以评估别人主张的价值,这不是无明是什么?到现在知识上的争论已变而为现实力量的对峙,由制度的矛盾发展成人类的生死存亡之争,这已经不是知识问题,而是存亡问题,其根即在于心灵的封闭,于是一方面要求自解,一方面要打击消灭敌人。在这中间,暴力固然可以合法化,卑劣之手段亦可以合法化。人与人之间不能再讲信任、同情、互爱,反之是恐惧、冷酷、残忍、傲慢,这不是人性上的大悲哀又是什么?对自己的心灵的丑恶反省极少,纵有反省,亦只是委诸外界现实力量的牵引,而不知自己的限制。佛教即要我们反观自己的心灵的无明,一切贪、瞋、痴、慢、疑、恶见……都是从这里来的,故非对治之不可。对治之道,即在扩阔自己的心灵,获取智慧,使自己从种种不同之见中超出;并在实践上改变自己的狭隘、怀疑、恐惧、冷酷的气质,使自己日进于高明之境,而不为无明所缚。这就是佛教安立种种智慧以超化众生分别性的烦恼与俱生性的烦恼的原因。对于今日自身尚陷于无明迷惘、不知病根的现代人,岂非正有对治之功?
“空”之智慧
“空”的观念是大乘佛教中观学派提出来的。从思想史上说,中观学派提出“空”的观念,目的是消除部派学者对“法”的执着。部派学者喜欢从分析的立场上了解一切“法”,目的是寻求各类现象的最后的存在情形。例如物质的现象(色法)列出十一种: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及无表色等。精神现象或心理现象则分别列出“心”、“心所”、“心不相应行法”等,后二者又各有数十种之多。此外尚有非现象意义的三无为法。部派学者认为:这些法就是最后的实在,各有其独立的性质(自性),更不可彼此化归为一。所以这是一种多元实在论的哲学。他们认为: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些法的独立性,则无法说明经验的来源,亦无法说明因果。但是,中观学派认为:法的独立性的赋与,是我们妄心(经验心识)活动的结果。因为妄心有分别作用,在它的作用之下,主客二分,主体遂以分别性的活动套上客体。经验、观念或概念都是这样产生的,所以对象的独立性,不过是主观经验的实体化,它自身并无这一独立的实体。
那么,它自身的存在状态是怎样的呢?中观学派说,它的存在是处于“缘起”状态:即不能自主、不能静止、不能自与其他存在的关连中切离出来的状态。相应于这种状态,一切观念均不能套上。这是以缘起观念来描述当下所经验的对象的存在情形,使其不能定着,以免为主体的分别活动套住。这可以说是存有论的用法。

中观学派即根据这一用法,进而提出“空”(Sunya)或“空性”()的观念来说明它。“空”并非虚无之义,而是指所经验之存在无独立性、无“体”,所以不能用概念来表述。一切存有之事为缘起,则一切均当体即空,如幻如化,无可定着,亦无可取着。能如此把握,即是如实观——由此可见,中观学派可谓远承原始佛教的精神,点明主观经验心识的活动永不能进入真实的领域。
不过,中观学派的这一个见解,并没有在他们的论书中清楚表达出来,也许他们不愿意违反自己反对以概念说空的前提,所以不愿意作正面的解释。他们的重要活动,依《中论》、《百论》的精神看来,是破斥一切企图以语言概念说最高真实的哲学。盖必破尽之后,方能呈显此一超语言之“空”态。于是,“中观”亦更无所说,言语道不断自断。另一方面,中观破斥一切言语概念,似乎亦在表明一切言语概念皆相依而立,因此亦可以互相抵消。因为依语言概念而成之理,不能离一观点,或一角度;换言之,在某一观点下,此理可成立,但若一离此一观点,此理即不成立。这种语言文字的性格,颇有点像康德所说的二律背反()。因此中观学派认为:凡有所说,即有正反两端,或有“四句”,彼此相害。如说“生”,即可分析出自生(A生A)、他生(非A生A)、共生(A及非A合生A)及无因生(A不由A生,亦不由非A生)四种情形,而四种均不合法。所以真正的真实,是必然自正反两端超出,亦即自语言的世界超出。所以,中观学派所向往之“空”,实是须经“双遣”后方能至的境界。在这一意义言,“空”可以说是对一切言说、一切对立的消解。换言之,“空”不但是存有论的概念,同时亦是表示双遣对破的方法论的概念。
在前一节中,我们已经谈到,人由于无明烦恼的限制,不能尽知别人的观点,而自我封闭,由此更生敌对心理,或傲慢自信,或憎怨仇视,互相伤害。若能观空,知所有由经验心灵所成之知识皆不能免执,皆不能免自我封闭,则知人所行之愚昧狭小,而求开拓消解。所以空亦可以说是一种消解的智慧,即以双遣对破来消解心灵上的执着。我们不否认现代人在处理具体问题上有成就,知识的分工亦使人类在不同的问题上各有所见,这可以说是一种建构的智慧,通过此,能把知识世界建立起来。但有建构即有消解,从知识发展的方向看来,人不能有完全的建构,故必须经常就所已建构者反省之,使之更进霍韬晦:佛教的智慧,是不是都能给予启发呢?,这是其一;知识世界领域甚多,人所能参与建构者往往只是其中的一小领域,人必须自知其限制,自虚其心,自空其说,以求容纳别人霍韬晦:佛教的智慧,是不是都能给予启发呢?,这是其二。由此看来,空的作用极大,现代人类社会能否各捐成见,免除分裂,即在于我们能否各自消解自身之障壁,去执成教,以成一共存互尊之社会。
中国佛教说“判教”之智慧
判教的活动在印度佛教时已有,虽然“判教”的观念当时未见。如《楞伽经》言顿渐,《华严经》言三照,《涅槃经》言五味,《解深密经》言三时,《法华经》言三车,以譬喻大小乘之别等等,都可以说是一种判教。不过这种判教在印度方面言,是显示思想义理之进展,亦与经典文献的出现有关。因为这些说法,多半是在大乘佛教初出的时候,面对从前的传统佛教的教义而作出的。它主要是强调自身资料的重要性,及晚出性,以争取群众及信徒的支持,所以自立门户的意味极重。印度的判教,从思想背景看,是以后出之义来统摄、批判前出之义。但中国佛教的判教情形,则有所不同,中国高僧大德在吸收印度传来的佛法时,不必知其经典产生之历史,但见种种资料皆佛所说,而义理方向有不同。既然诸经都是佛所说,为什么其中会有不同呢?为了表示佛教乃一大系统,各经典之间亦有其有机之联系,这些不同之资料即有融通的必要。融通之后,即见其不相碍,诸经典之间皆有桥梁可通。换言之,这种做法就是要求我们不可只陷在一个资料中,而应该互换观点,即“互观”,以见双方皆有其价值,亦各成就一义理方向,然皆不离佛陀慈悲救度众生之大业。以此互观作起点,再进一步要求从一切可能观点对一切已成资料之“遍观”。遍观,即将我们的心灵扩充至极,以容纳种种义;反面说,也就是把我们陷于一隅之见的妄心一一去掉,于是可以汇成一大义理世界,而各各不相碍。这是一个至美、至庄严、而又至和谐的世界,其成就即由“互观”以至“遍观”而得。由此看来,判教的工作,也就是要形成一总持的智慧,以总持一切经典的价值。
在中国佛教中,真正构成一个严格的判教系统,以总持当时一切传入的佛典的,是天台与华严两教派。天台判教,先设标准:一以说法之先后次第分,此即“时”,二以说法之内容分,此即“化法”,三以说法之方式分,此即“化仪”,合为“五时八教。通过“时”、“法”、仪”三观念,遂将佛陀一代所说之教法总持起来。及至华严宗兴,其所走之圆教之思路与天台不同,天台是从“法性”的观念入,着重心灵对法性的把握,由此而历种种观以成圆观,故天台从内容上分佛法为“藏、通、别、圆”四教,各教所观境皆不同。例如四谛之理,在藏教所说的是生灭四谛,通教所说是无生灭四谛,别教所说的是无量四谛,圆教所说的是无作四谛。无作,即表示心灵的分别活动于此已不再相应,“作”的观念已去除,现象上的法已消散,法性已自一切主观之观法中豁出,所以说这是一圆观。在此圆观之作用下,人乃能证见一切法皆涅槃之理,而如如相应。比较起来,华严是从“真心”的观念入,着重心灵活动所创生之境,由此而立五教:小、始、终、顿、圆。内容之分别即在小乘只言六识;始教中虽说唯识,而及于阿赖耶,但不及于如来藏;终教则知此阿赖耶识自另一义言之,即为如来藏;顿教则显一切法皆唯一真心。至华严圆教更大彰此真心之全幅大用,性海圆明,无碍自在,以彻入一切法,而“一切即一、一即一切”,所以说这是无尽缘起,亦即由佛之心灵所开出之无限之庄严、美丽之世界,这亦是心灵升进后所得之圆观。由此我们可领悟华严之所以改判五教及特别重视《大乘起信论》的原因。
华严除以“教”开宗外,同时亦以“理”开宗,而判分为十。为免繁琐,此处从略。但它的精神,即在于显示义理之层次,由小乘教而次第上升,最后进至华严境界。这即是一义理层级的安排,由有归空,再见真实不空,如是即将一切佛义、佛理收摄其中而总持起来。
由此看来,天台、华严之圆教内容虽不同,但其判教之智慧则一。目的都是总持佛法,把各种义理分别按其层级、方向安设起来,使各义理不相障碍,但随人心之游赏贯通。人的问题,在对一家之义起执:一方面封闭自己,一方面抹杀他家他理之存在,于是人之世界分裂,相轻相害,终至生大苦。也许人生之无明非得吃大苦、付大代价不能超化。智慧之来,原非轻易。由此我们回顾上文所说的人生无明烦恼的反省,这是人类悲剧产生的内在根源,故必须转出智慧以消解之。但在客观上,此智慧之出,又关乎对别人义理之了解,所以判教之智慧,尤为必要。今时世界四分五裂;人心浮嚣。究其原委亦是知识世界分裂的结果。西方文化原是一重智而向多方活动之文化,故其所成立之知识世界,亦是一分途独立、各自发展的世界。
以上所讲,条列了佛教的四种智慧。从内容上说,实不足以尽佛教智慧的全部。不过,对应现代人心,也许这四种智慧是最急需的。我们说:如实观是一种客观开放的智慧,对烦恼的体认与对治是一种实践和反省的智慧,空是一种消解的智慧,判教是一种总持的智慧。智慧虽分四种,但在精神上却是一贯的,最先都是依于对人生的如实感受而开出。人若能于此一念涉入,即能证见佛所说的种种境界,而知其智慧为不虚了。(蔡敷治记)
(原载《法住丛书》①《佛教的现代智慧》)
[香港]霍韬晦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