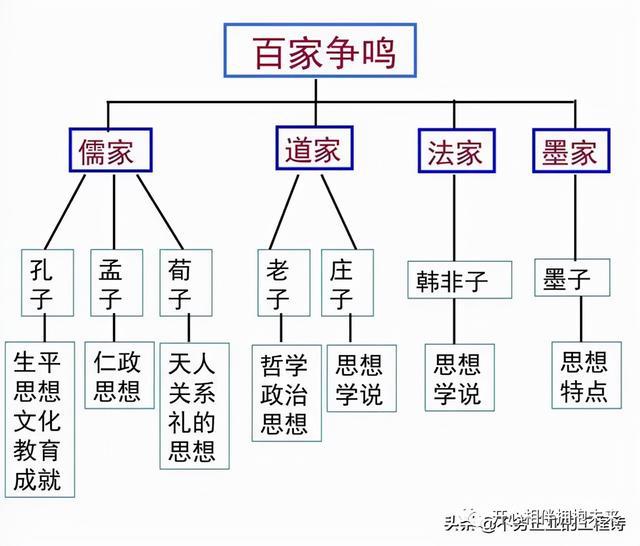陈撄宁写的论《四库提要》不识道家
法家出自道家的
《韩非子》收录在道藏之中,在儒家修四库全书时,将道家经典强行分离开来。详细请看陈撄宁写的论《四库提要》不识道家学术之全体
《韩非子》有《解老》、《喻老》诸篇,对于老氏之说,可谓别有会心。太史公有名庄申韩合传,言申韩惨檄少恩,皆原于道德之义。又谓韩子言刑名法术,而归本于黄老。夫韩非之书,虽为人所垢病,然其学实由道家而出,精要处颇多,不可以耳为目,一概抹杀之。编集《道藏》者,已见及于此矣。
论《四库提要》不识道家学术之全体
读马端临《文献通考》,见其于《道藏》书目条下,作一按语日:"道家之术,杂而多端,先儒论之备矣"云云。后人遂执此言以为道家病,凡《道藏》所收各种书籍,除对于道教有直接关系者而外,皆认为不应列入《道藏》中。《四库全书提要》批评白云霁之《道藏目录》云:"所列诸书,多捃拾以足卷肤。"意谓诸书多与道家无关,因编者欲臻满卷数,故尔随便拾起几种,以壮观道教门庭而已。其由《道藏目录》中剔出各书名如左:
《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易象图说内外篇》,《易筮通变》,《易图通变》,《易外别传》(《四库提要》谓旧皆入"易类")。
《素问》,《灵枢经》,《八十一难经》,《千金方》,《肘后备急方》陈撄宁写的论《四库提要》不识道家,《急救仙方》,《仙传外科秘方》,《本草衍义》(《四库提要》谓旧皆人"医家类")。
《黄帝宅经》,《龙首经》,《金匿玉衡经》,《玄女经》,《通占大象历》,《星经》,《灵棋经》(《四库提要》谓旧皆入"术数家类")。
《鬻子》,《曷冠子》,《淮南子》,《子华子》,《刘子》,《意林》(《四库提要》谓旧皆入"杂家类")。
《华阳隐居集》,《击壤集》,《宗玄集》(《四库提要》谓旧皆入"别集类")。、
《太玄经》,《皇极经世书》(《四库提要》谓旧皆入"儒家类")。
《公孙龙子》,《尹文子》(《四库提要》谓归皆入"名家类")。
《墨子》(《四库提要》谓旧入"墨家类")。
《韩非子》(《四库提要》谓旧入"法家类")。
《孙子》(《四库提要》谓旧入"兵家类"),
《鬼谷子》(《四库提要》渭旧入"纵横家类")。
《江淮异人录》(《四库提要》谓旧入“小说家”)。
《穆天子传》(《四库提要》谓旧人"起居注类")。
《山海经》(《四库提要)谓旧入"地理类")。
编辑《四库提要》诸君,又谓上列各书之分类,"虽配隶或有未妥,门目或有改易,然总无以为道家言者,今一概收载,殊为牵强。"且将《道藏》与《佛藏》相提并论,谓"二氏之书往往假借附会,以自尊其教,不足深洁。"伊等不知当日编辑《道藏》之人,具有特别眼光。一面既欲抵御外教之侵略,不能不利用本国整个的文化以相对抗;一面又高瞻远瞩秦汉以前诸子百家之学术,皆起源于道家,故将各家著作择其要者,录取数种于《道藏》中,亦无不合之处。
时贤震于《文献通考》为九通之一,夙负盛名。《通考》既诮道家"杂而多端",而《四库提要》一书,又是治目录学者之金科玉律,其言更可与《通考》互相印证。于是道家学术益遭世人厌弃,每每数典而忘其祖,甚至据释氏之理论以攻击道家,尤觉荒谬。其无识亦与今日欲持全盘欧化以改造中国者相同。本篇非宗教论文,故亦未遑置辨。
《汉书·艺文志》谓:"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术也。"据此则知道家学术,即是治国平天下之学术。含义甚广,不可执一端而概其全体。《尚书》、《春秋》所记载,固不外乎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即全部《易经》所记载,又何尝不是此道?何尝不是人君南面之术?
古代艺文皆掌于史官,民间颇难得见。当日老子实任斯职,孔子若非得老子许可,恐末必能全窥六艺之文。昔道祖老子,许传《易经》今《道藏》全书,反不许收《易经》一类著作,亦可怪矣。果《易经》与道家无关,魏伯阳何以作《周易参同契》?陈希夷何以传先天八卦图乎?
医道与仙道,关系甚为密切,凡学仙者,皆当知医。故将医书收入《道藏》,自是分内应有之事。况《千金方》作者孙思邈,及《肘后方》作者葛洪,皆道门中之铮铮者,更不容漠视。《素问》、《灵枢》为医家之祖,黄帝为道家之祖,《素》、《灵》二书,纵非黄帝自作,亦是黄帝遗传之学术。《道藏》中关于黄帝一派之书,本嫌其过少,收几部医学家典籍,又有何妨?
术数之学,不外乎阴阳扩阴阳家为九流之一,亦源出于道家。所以阴阳家有《黄帝泰素》二十篇,又有《南公》三十一篇,《项羽本纪》载楚南公之言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注谓:南公者道士,识废兴之数。试观后世《太乙》、《奇门》、《六壬》诸书,皆托始于黄帝,而种种图谶碑记预言,非诸葛亮即刘伯温,盖常人心目中,久存一"惟有道之士方精于此"之感想。可见阴阳术数,乃道家之副业,亦犹农家种植五谷而外,必兼理蚕桑耳。就令所有术数书籍,一概收人《道藏》,亦不为过。
淮南王刘安从八公学道故事,人皆知之。淮南鸿烈书中,形容道之玄妙处,亦可谓淋漓尽致。讲道家之文章,除老庄而外,当无胜过《淮南子》者。杂家之学,不过本道家真义而推阐之耳。岂可谓杂家驳而不纯,遂摈于道家门墙之外乎?又如《曷冠子》,在《汉志》原列入道家,其书虽涉及刑名,而大旨本于黄老,韩昌黎颇喜读之。作者不详姓氏,相传为楚人,居深山,以曷羽为冠,故名,盖亦道家之流也。《意林》,唐马总编,书中抄集老庄管列诸家言,多与今本不同。可视为道籍中之参考书。以上三种,收入《道藏》,未见有何龃龉处。
《华阳隐居集》,陶弘景作。《击壤集》,邵康节作。《宗玄集》,吴筠作。弘景本道家知名人士,不必论。邵子之说,出于陈希夷,与程朱之笃守儒教门庭者迥异。希夷先生,既经世人公认是道家,则康节先生著作怎么学道家思想,亦未尝不可列入《道藏》。吴筠文章,多半趋重仙道方面,对于道家,不为无功。况吴本人在唐天宝时,自请隶道士籍,则《宗玄集〉之收入《道藏》,亦固其所。
尹文子虽为名家,其学亦本黄老,故其书以"大道"二字名篇,虽亦泛论治理,而重在正名核实。《庄子》称其"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颇有合于老氏之旨。是盖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者。
公孙龙之徒,虽为庄子所不满,然其立论,颇近于道家之玄谈。昔贤谓公孙龙伤明王之不兴,疾名器之乖实,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寄白马而齐彼我,冀时君之有悟焉。可知其书自具深意,非只以诡辩为能事者。《汉志》云:"道家出于史官",“名家出于礼官”,而掌礼乃史之专职,礼官史官,二而一者也。是名家与道家,亦同出一源。《道藏》之有名家,殆如《释藏》之有因明乎。
老子三宝:"一日慈,二日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墨子皆得之。《兼爱》,《非攻》,"慈"旨也;《节用》,《节葬》,"俭"旨也;《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等篇,皆极尽守卫之能事,自处于被动之地位,而对于先发制人之战略,则绝口不谈,是真能笃实奉行"不敢为天下先"之古训者。《庄子》书中,除关尹、老聘而外,独赞墨子,或亦因墨子之学近于道家故耳。墨家素为儒家所排斥,而墨子亦有非儒之篇,儒墨根本难以调和,只有请其加人《道藏》而已。
《韩非子》有《解老》、《喻老》诸篇,对于老氏之说,可谓别有会心。太史公有名庄申韩合传,言申韩惨檄少恩,皆原于道德之义。又谓韩子言刑名法术,而归本于黄老。夫韩非之书,虽为人所垢病,然其学实由道家而出,精要处颇多,不可以耳为目,一概抹杀之。编集《道藏》者,已见及于此矣。
自古道家,无不知兵者。所谓有文事必有武备也。若专尚清静无为,其何以靖内忧而攘外患乎?如黄帝、力牧、风后、封胡、伊尹、太公、管子、曷冠子、文种、范蠡诸人,在兵家皆有著作。虽其书不传,然班氏《艺文志》及刘氏《七略》,皆载其书名。盖道家最善于沉机观变,不轻举,不妄动,老谋深算,施于战阵,常操必胜之权,故兵家遂有道家之特长,非此不足以定大业。《汉志》道家,亦有《孙子》之名,故《道藏》收《孙子》,未为创例。
《鬼谷子》,《汉志》不录,《隋志》入纵横家。其书有《捭阖》、《反应》、《内楗》、《抵(左“山”右“戏”》、《飞钳》、《忤合》、《揣》、《摩》、《权》、《谋》、《决》、《符言》十二篇,又有本经《阴符》七篇。《战国策》云:"苏秦发书陈箧,得太公阴符,简练以为揣摩。"可知纵横之学出于太公。而太公当然是道家人物。鬼谷子既服膺太公之学,而自隐其姓名,不欲表现于当世。《史记》又言鬼谷子长于养性治身,是必有味于道家之精意者。苏秦、张仪得其皮毛,已足以玩侯王于股掌,取卿相如探囊。而鬼谷子反敝屣功利,遁迹山林陈撄宁写的论《四库提要》不识道家,恬淡自守。观其书中有云:"盛神法五龙,养羔法灵龟"诸奥语,非深于道者孰能之乎?将其书列入《道藏》,可谓名实相副。
扬子《太玄经》,邵子《皇极经世》,皆《易》之支流。《易经》哲理,既与道家相通,此二书之收入《道藏》,自无问题。
《江淮异人录》所纪多道流、侠客、术士之事,《山海经》语涉神怪,《穆天子传》迹遍遐荒,诸如此类怎么学道家思想,皆儒家所不敢言。道家思想,本是游乎方之外者,故不妨接受耳。
总而言之,道家学术,包罗万象,贯彻九流,本不限于"清静无为"消极之偏见,亦不限于"炼养"、"服食'、"符篆"、"经典"、"科教"狭隘之范围。《道藏》三洞、十二部之分类,诚不免疏舛;但此或受佛教之影响怎么学道家思想,出于不得己。
吾人今日谈及道教,必须远溯黄老,兼综百家,确认道教为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寄托。切不可妄自菲薄,毁我珠玉,而夸人瓦砾。须知信仰道教,即所以保身;弘扬道教,即所以爱国。勿抱消极态度以苟活,宜用积极手段以图存,庶几民族尚有复兴之望。武力侵略,不过裂人土地,毁人肉体,其害浅;文化宗教侵略,直可以夺人思想,却人灵魂,其害深。武力侵略我者,我尚能用武力对付之;文化宗教侵略我者,则我之武力无所施其技矣。若不利用本国固有之文化宗教以相抵抗,将见数千年传统之思想,一朝丧其根基,四百兆民族之中心,终至失其信仰,祸患岂可胜言哉!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