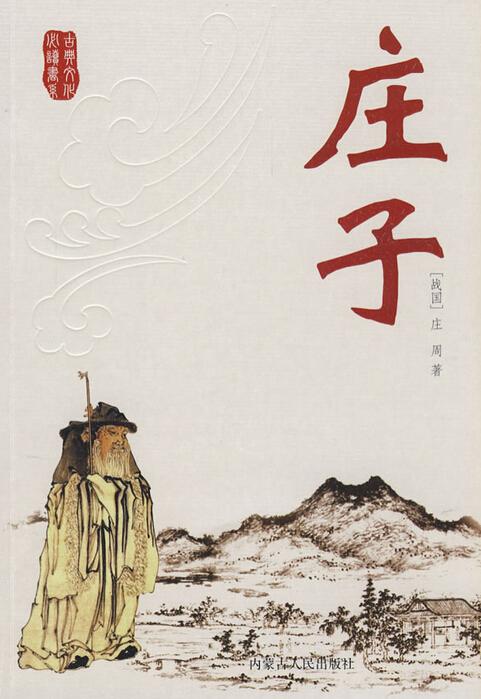李大钊:时有今古的质态既殊今古
李大钊的历史理论当中最具特色的部分要算时论。在这个问题上,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如前所述,他的早期思想源于爱默生。他同意爱默生的看法,“今”是世上最宝贵的东西,它为人类的创造活动提供了无限的机会。无论是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还是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在哲学上都着力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为了创造美好的未来,必须立足于今,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内在的积极性。为此,他尖锐地批评了所有忽视“今”与人的内在积极性的思想。

最初,李大钊的时论建立在一种先验哲学的框架中,这种哲学坚信宇宙中存在着一种在无尽的宇宙和无数个人的“自我”中流淌的“大实在的瀑流”,一种普遍的青春精神。这条瀑流辩证地运动着,并在不断的“流转”中展现自身,而这种“流传”通常出现于“今”的无限系列中。李大钊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依然在自己的著作中宣传这种先验的哲学观念,而且对“今”的感情升华使他在很大程度上超脱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1923年初,他发表了一篇题为《今与古》的论文[23]。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重申了上述哲学观点:“宇宙的运命,人间的历史,都可以看作无始无终的大实在的瀑流,不断的奔驰,不断的流转,过去的一往不还,未来的万劫不已。于是时有今古,人有今古,……今古的质态既殊,今古的争论遂起。”因此,这种“今古的争论”成为文章的主题。李大钊写这篇文章的要旨在于反对历史编纂学当中的“怀古派”。为此,他对一部分欧洲17—18世纪的哲学家的著作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研究,如让·博丹、弗朗西斯·培根、笛卡尔以及英国神学家乔治·黑克威尔,他把这些人看作是“崇今派”,从他们的理论中得到了重要的启示。他指出:“鲍丹(即博丹)学说的重要,不在他的君政论,而在他企图立一普遍历史的新学说,以代中世时史学界流行的黄金时代说( of Age)。”[24]培根则发现“循环说为知识发展上最大的障碍,每致人们失所信赖与希望”[25]。笛卡尔敢于批评古代权威和古典文化的精神令人可敬。而黑克威尔认为,历史“退落说可以腐痹人的元气,世界普遍衰朽论,销沉了人的希望,钝滞了人的努力的锐利”[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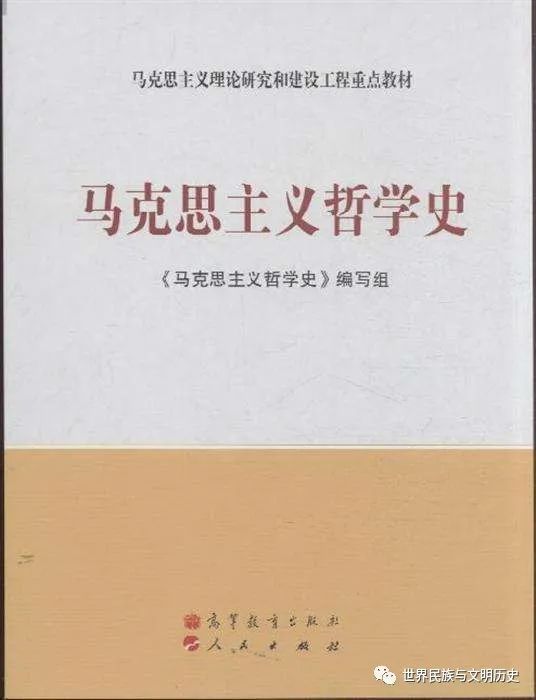
李大钊认为,上述观点表明这些具有“乐天努力的历史观人生观”的启蒙哲学家都有正确的时代观,也就是说,他们崇今。这种观点与爱默生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爱默生主张:“昨日不能唤回,明日还不确实,你能确有把握的,就是今日。”[27]李断言,这种时代观能够激励“为今人奋力,为来者前驱”[28]。
1923年11月,李大钊发表了《时》,这篇文章重复了他过去的哲学观点,明确地阐述了对时的领悟与对历史的理解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说:“一生最好是少年,一年最好是青春,一朝最好是清晨,……天运人生周行不息,盈虚消长,相反相成。逝者未逝,都已流入现今的中间,盈者未盈,正是生长未来的开始。时是无始无终的大自然李大钊:时有今古的质态既殊今古,时是无疆无垠的大实在。……时是伟大的创造者爱默生的自然思想和道家思想有什么不同,时亦是伟大的破坏者。历史的楼台,是他的创造的工程。历史的废墟爱默生的自然思想和道家思想有什么不同,是他的破坏的遗迹。世界的生灭成毁,人间的成败兴衰,都是时的幻身游戏。”[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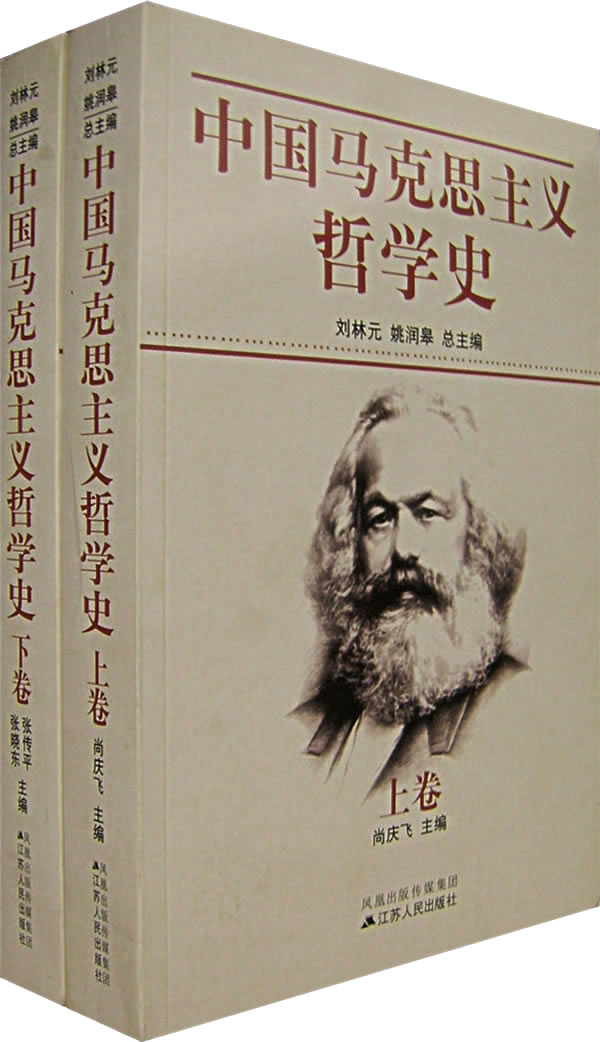
对李大钊来说,时有着玄妙的含义。从中国的道家到西方的哲学家、心理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都曾试图尽力说明这个问题,但迄今为止,“都只能与吾以一部分的解答,不能说出他的真实的全体”[30]。这是因为:“时的问题不能研究,且亦不必研究。说来说去,言人人殊,时的问题,真是不可思议。”[31]如果“时”如此变幻无常、难以捉摸,以至于不能真正被人认识;那么,我们就必须紧紧把握住我们所能理解的东西,这就是今。因此,李写道:“过去未来,皆赖乎今,以为延引。今是生活,今是动力,今是行为,今是创作。苟一刹那,不有行为爱默生的自然思想和道家思想有什么不同,不为动作,此一刹那的今,即归于乌有,此一刹那的生即等于丧失。”[32]
这种珍惜片刻的感情促使李大钊萌生了一种想法,在他看来,人生在世,每个人都有无限的美好机会,为了不失去这种机会,必须最充分地利用他们占有的每一时刻。他还认为,只有了解历史,才能珍视今天的创造机会。对时的错误认识必然导致对历史的错误理解,而对今的错误估价也同样会产生错误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是逆退的,是静止的,是背乎大自然大实在进展的方面的,是回顾过去的,是丧失未来的”[33]。但是,“要知时的首脑,不在古初,乃在现在,不是向广漠无涯的过去奔驰,乃是向广漠无涯的未来奔驰”[34]。如果谁把今看作是“时的首脑”,那么,谁就“能得到一个奋兴鼓舞的历史观,乐天努力的人生观”[35]。
李大钊关于时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主张现在包含着过去,而且为未来作准备,要放眼未来,对未来充满理想。这些都符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然而有必要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现未来社会主义理想的历史进程是有相对严格的历史时代规定的,而过去在时间上则是根据特定的、必要的历史发展阶段所区分的。这种历史发展阶段是具体的社会经济运动的结果。不仅过去如此,未来也是被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限定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就被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即资本主义的崩溃时期。
此外,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客观决定作用不仅适用于过去和将来,而且也适用于现在。马克思认为,人们创造历史,但仅仅是在特定的先决条件下创造历史。“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36]
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并不是所有的时机都对革命有利。实际上,有利的时机是相当罕见的。这种时机的出现,是由生产力运动决定的。只有当生产力的发展造成引起革命的社会政治条件以后,才能产生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时机。所以,正如卡尔·曼海姆已经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把时间看作是“一系列战略点”[37]。而不是像李大钊所主张的,时间是一系列意义均等的“今”。同样,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能动性也并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它建立在承认决定性和历史的客观作用基础上李大钊:时有今古的质态既殊今古,同时亦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它以对任何历史时机都作具体的分析为依据。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一般是根据他们对历史决定力量的分析,对政治行动作出不同的规定。然而,无论如何,他们的行动要符合客观的历史条件,而客观的历史条件对革命的冲动起限制作用。这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显著特色。
李大钊的历史观几乎完全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特殊的理论原则,他的时论基本上排除了以客观历史发展为基础的时代区别,他崇尚的今除了具有创造性和活力以外,没有任何时代意义。在展望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时,他并不注意历史的客观力量所起的作用,而是强调人的革命愿望和革命觉悟。他认为,这种愿望和觉悟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正确的时间观念,也就是说,要使人们都知道在“今”当中存在着内在的潜力。应该说,李大钊所说的“今”意义十分含蕴,人们需要通过自己的行动去理解实现无限的内在机会的真实含义。既然存在着一系列无限的“今”,那么可以说,李的时论就是一种永远行动的哲学。
李大钊的历史理论也是一种能动的哲学。它要求历史研究的首要目的不是去发现作为政治行动基础的客观历史发展趋势,而是创造一种从事政治活动的心理环境。历史理论的作用不在于使人们从历史当中获取科学的想象力,而是提供给人们一种勇于创造未来的精神力量。在李大钊看来,受到一种“正确”的历史观(以及正确的时论)的鼓舞下,人们会去塑造历史;他们不会被历史所束缚。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儒家思想对大学生的影响论文 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论文[1]1](https://guoxue.pro/public/static/common/images/not_adv.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