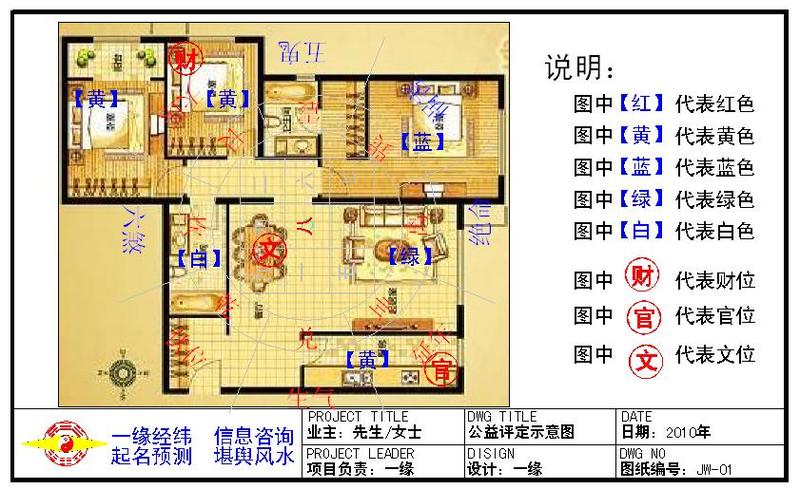有关《声无论》音乐美学思想评价的若干问题

有关《声无哀乐论》音乐美学思想评价的若干问题
魏晋时期文学家、思想家和音乐家嵇康(223―263)撰写的《声无哀乐论》,自问世后其思想向为历朝历代人关注。直至20世纪的近代中国,当人们在学习、研究了中国以及西方、东方的音乐美学思想之后,对《声无哀乐论》这一笔古代遗产的思想价值,不但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并且在对具有不同民族文化特征的音乐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中,看到了这一古代智慧的不朽。从其在思想史上的价值来看,《声无哀乐论》的思想,也为今天建设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音乐美学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即使从今天中国音乐美学的学科理论建设来看,这部论著也从学理层面提供了至今看来仍然富于启迪、依然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认识成果。
对于《声无哀乐论》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近二十年来,逐渐成为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研究的“显学”,并且,其研究成果也成为音乐美学课堂教学及研究性学习的重要内容。在当代中国音乐美学研究和课程教学中,《声无哀乐论》成为重要的学习内容和必读文献,与《乐记》、《溪山琴况》一起成为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研究中最受人关注的三部经典性著作。与此同时,在不同的研究者之间,对嵇康“声无哀乐”理论的认识和评价,是既有共识,又有分歧,甚至与一些相关理论问题的讨论和评价产生关联。我个人也曾在研究生教学中,组织过有关的讨论,经常要面对和解答学生的提问。在此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一些问题,并形成一些认识。也觉得有必要将这些问题和相关的认识提供给同行和学生,以供讨论。因此,有关对《声无哀乐论》音乐美学思想的评价,笔者在此提出在研究和学习中需要关注、并且值得认真思考的六个方面的问题,以飨读者。

1、嵇康对儒家传统礼教叛逆的原因以及对其音乐观的评价
从《声无哀乐论》文中所设东野主人(代表嵇康本人思想)和秦客(代表儒家思想)最初的辩难中已经可以看出,双方的论辩首先是围绕对儒家传统音乐观的评价而展开的。但是,这里的评价,从其主要的倾向来看,仍然属于学理层面上的讨论,与对礼教的批评并无直接关系。例如儒家传统音乐观念中的“声有哀乐”思想,也是至今一般人所拥有的观念,并不能说主张“声有哀乐”,就是儒家的音乐观念了。但是,嵇康讲“声无哀乐”,在魏晋时期,却是有对儒家传统礼教的叛逆这样一个思想背景的。有关叛逆的因由,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称嵇康“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分析其原因,是因为他对当时统治者虽提倡儒家礼教却又非常的虚伪很是不满,“不平之极,无计可施”,于是反对礼教,但其本心仍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甚至比司马氏“要迂执得多”。这里说嵇康“相信礼教,当作宝贝”,表述上确有不妥,是讲过头了。但是,若认为嵇康实际上是因为司马氏集团表面上提倡名教,实际上却争权夺利、排除异己、具有十足的虚伪,再加上他所处的时代有老庄哲学为魏晋名士的处世提供精神支持,因而以激烈的态度“越名教而任自然”,应当是能够理解的。但是,这样的态度,也并非导致从本质上全然排斥儒家传统礼教。就嵇康的个人处世态度而言,就真的与传统礼教毫无关系了吗?嵇康在《家诫》中要其子遵循“忠臣烈士之节”,这在当时实际上已属儒家传统道德范畴之内的行为准则,并要他处世谨小慎微、明哲保身,说明他在处世态度上(如何教子也是处世态度之一种),也并非叛逆到与传统礼教毫无关系。
再回到嵇康音乐观与传统儒家音乐观的关系上来,这方面,日本学者原正幸指出,在《声无哀乐论》的“第八问答中看到道家音乐观和儒家音乐观的交错影响。这是由于嵇康根据作为杂家的《淮南子》的音乐观而使其礼乐批评的基本论理更缜密地发展”,并且指出“不能单纯地说嵇康否定了儒家的音乐观,而应该说他是超越了传统儒家的音乐观”,这是很有见地的论点。①在嵇康之前,我们在秦汉道家的代表性著作中,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都可以看到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吸收儒家等诸家思想而构成新的思想体系的特点,而这些在《声无哀乐论》的第八难中也有反映。其中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之为体,以心为主”,又讲“为可奉之礼,制可导之乐”,对“先王用乐之意”以解释,明显是汲取了儒家音乐思想中的一些概念和观念,但是这些都是以道家思想为基础的。因此,就嵇康音乐思想中道家音乐观和儒家音乐观的某种联系而言,准确地讲,不是接近、更不是全然无关,而是汲取、借用甚至超越。
有关对嵇康音乐思想的价值评价,如果对以嵇康为典型代表的魏晋名士特有的处世方式有所了解,便会知道,这些名士的所作所为,其实是社会上一群极具个性、行为特殊的人士所为,这类行为的产生,也是特殊社会环境的产物。这些名士的行为、观念,虽然确有追求个性解放的特点,但就其社会性而言,决非能代表大多数人的行为和观念。更何况,直至今日道家的音乐思想主张,“声无哀乐”的观点,包括其中确有很高思想价值的论点,也并没有成为普遍的观点。
2、嵇康讲“声无哀乐”并非否认“乐有哀乐”
在《声无哀乐论》中,“声(音声)”不等于“乐”。“乐”的存在,是根本的存在,而作为“乐”中之“声”的“声(音声)”,是作为“乐”的一个要素而存在。如果要追究《声无哀乐论》关于音乐本体或者音乐存在方式的认识,究竟是“乐本体”还是“音本体”,那么,可以明确地回答,是“乐本体”。②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我们就会明白,嵇康讲“声无哀乐”有关《声无论》音乐美学思想评价的若干问题,但并非否认“乐有哀乐”。既然已经承认或理解到,嵇康之所以能够讲“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躁静者,声之功”,就说明他已经认识到音声能对人产生情绪上的影响;但是,如果再看到,与此同时,嵇康实际上也已经说明了人的哀乐情感是由社会生活中产生的(“自以事会先构于心”),而这种哀乐情感,是会在“乐”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那么,在《声无哀乐论》中,“声无哀乐”和“乐有哀乐”并非是相互排斥的概念,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与一般人简单地在“音声”与“哀乐”情感之间,建立某种直接对应关系的见解不同,嵇康只是更加强调在“乐”的活动中“心”的作用(“乐之为体以心为主”)。所以,嵇康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割断人的情感与音声的关系,他只是不把这种关系绝对化、固定化。据此,如果仅仅以嵇康讲“声无哀乐”,就认为他是完全否定了音乐的音响与人的感情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而认为这是其理论上的致命弱点,那么,只要论证在音乐生活中,音声与特定感情的发生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对应关系(在文化差异依然存在的条件下,这种情况仍然存在),这种评价就是一种对嵇康“声无哀乐”理论的误解。这方面,潜伏着的理论危机是,在对嵇康理论的译读和对其论点的分析中,笼统地用今人使用的“音乐”(通常视为“音”)的概念,来模糊嵇康已经在理论上给予 区别、并且分别作为立论依据的“乐”与“音”的概念区分,结果造成评价上的误解。其实,在“乐”的范畴中,“音声”加上“心”的哀乐情感,是可以构成“有哀乐”的音乐体验的。

3、“文化差异”与“文化认同”作为不同的认识前提而导致认识上的差异
就嵇康“声无哀乐”立论的依据而言,其中很重要的方面,他是通过强调文化的差异而论证其观点的合理性,这同代表传统儒家音乐思想的《乐记》,以文化认同为认识基础,通过强调“人心之感于物”的普遍性,来论证制礼作乐的必要性,正好形成明显的对比。这也反映在《声无哀乐论》中东野主人与秦客的辩难中。嵇康对于文化差异性的认识,简括起来就是两点,一是讲文化心理方面的差异(“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一种是情感心理方面的差异(“理弦高堂而歌哭不同”)。从中国音乐美学思想史上看,在认识上能够讲文化的差异,并以此为据探讨音乐审美现象的多样性、非一致性,比之简单地讲文化认同,要深刻得多,理论贡献也往往大得多。
同样与对嵇康“声无哀乐”理论的评价有关,一般人在对待音乐审美中的特殊现象时,经常是以文化认同为其认识前提,从而认为其理论不能成立、甚至认为是诡辩。但是,如果从文化差异的认识前提来看待其理论,则会发现,所谓“声无哀乐”或音声之“无常”现象,的确是存在着的。嵇康讲的“殊方异俗,歌哭不同”的音乐现象,在今天的学术视野中,就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差异现象。因此,如果只是取文化认同的角度而对嵇康的理论做否定性的评价,显然是片面的。即使在今天,从一些音乐人类学者的调查事例中、甚至从日常生活的音乐事例中,也仍然可以找到“殊方异俗,歌哭不同”现象的存在。顺便说一句,如果在音乐美学研究中,无论是从认知的角度,还是从文化的角度,能够引入更宽的学术视野,就不会做出偏于一端的价值评判来。这是一个可以做进一步的展开、做专题研究的课题。
4、《声无哀乐论》并不是中国的自律论音乐美学著作
有关对嵇康音乐美学思想价值的评价不少人将嵇康的“声无哀乐”理论,与西方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这部被认为是西方自律论美学代表性著作的思想做比较,认为两者都注重音乐的形式,注重对音乐特殊性问题的探讨,因而将《声无哀乐论》也视为中国的自律论音乐美学著作。其实,音乐美学上的自律论问题,固然可以从认识论的角度,对音乐审美的特殊性、确定与不确定性、乐音的构成与表现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但是,所谓自律论的问题,从认识上讲,并不仅仅是认识论的问题,而是有更深层的、即本体论的理论前提。这方面,只要在理论上看到了“乐本体”与“音本体”在本体论方面的“理论分型”,并且了解了《声无哀乐论》在有关本体论的认识上有关《声无论》音乐美学思想评价的若干问题,实际上仍是以“乐本体”为其理论前提③,同时也认识到“音声”不等于“乐”、“声无哀乐”并不等于“乐有哀乐”,也就不会简单地将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作为自律论音乐美学思想来对待了。随着中西音乐美学研究的深入,我们已经不应仅从表面上对中西音乐美学的特点做横向比较,而是应当首先从分析其思想内涵人手,继而对中西音乐美学思想的不同特质或者在何种层面上具有相似处、又在何种层面上有所不同,给予更深入的认识。

5、在“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的前提下,嵇康并未完全割断音声与情感之间存在的联系
通过对音乐审美中情感情绪概念的区分和重新界定④,并将此理论作为一把“刀子”来剖析嵇康的“声无哀乐”理论,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在“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的前提下,嵇康并未完全割断音声与情感之间存在的联系。嵇康若是只讲“躁静者,声之功”,则只是看到了音声能够引起人的躁静情绪这个现象,但是进而讲到“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注:此中的“情”,是情感而非情绪之“情”),则是明确地讲了音声与情感之间存在着的联系、以及情绪(“躁静”)在两者关系中起的中介作用。因此,“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的表述,比之于“躁静者,声之功”,在嵇康“声无哀乐”理论的整体构成中,具有更为特殊的价值和意义,这也与对其理论价值的评价有关。
另外,需要认识的是,针对音乐审美中的“无常”现象,嵇康强调“心”的作用,并将音声与情感的联系,限定在“躁静”的情绪反映这一中介环节上。但是,针对音乐审美中的“有常”现象,这一论点则会让人认为似乎是割断了音声与情感之间的联系。其实这里反映的,正是前面讲到的“文化差异”认识前提和“文化认同”认识前提的区别。可以说,嵇康是在“文化差异”的认识前提下,强调了音乐审美中的“无常”现象。因此,需要补充的是,在“文化差异”认识前提下,不能说强调了“无常”现象的存在,就是割断了音声与情感两者之间的联系。所以,一般性地以嵇康否认音乐能表现哀乐情感、否认音乐的音响与人的感情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便认为其论点是完全错误的,这样的看法,在认识上是只讲了“文化认同”的认识前提,而忽视了“文化差异”这一同样可以在许多情况下作为现实依据而存在的认识前提。
6、有关嵇康“声无哀乐”在社会学方面的理论意义和相关评价
嵇康的“声无哀乐”思想,不仅有音乐美学思想方面的思想价值,并且还有更大范围的思想价值。虽然目前人们对这一思想的认识,还主要是在学术领域而非社会实践领域,但是,在社会学领域,“声无哀乐”的思想具有特别的意义。从音乐美学的角度讲,“声无哀乐”在音乐实践和理论研究中,主要是用于对音乐活动中音乐审美的特殊性及其规律、特点的了解,但是,若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声无哀乐”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经常呈现的是“他人即地狱”、个体思想行为会经常被人误读、误解的一面,另一方面隐含的是个人可以坚持自己所思所为、不从俗流的一面。从这点上讲,“声无哀乐”在今天一般人的观念和处世方式上,不论是从音乐学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不论是学理上的独到识见还是个性上的不从俗流,真正认同者仍然是少数,何以言其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心声?
对于《声无哀乐论》理论的认识,有不少论文、教科书都提到该书“有诡辩论因素”(甚至把差异性、特殊性当作诡辩来看待)。用今人的观点来看待《声无哀乐论》文中主客辩难的表达方式,确也可以从辩难中某些比喻的不恰当做出这样的评价。并且,这样的评价,似乎不需做深入了解,便可让人认同。但是,对一个理论的评价,不论是持何种评价观点,都应尽力在确实做了深入了解的基础上道家的音乐思想主张,然后再做判断和评价。但是,如果未对“声无哀乐”理论有更深入的理解道家的音乐思想主张,甚至将其中一些涉及文化差异性、音乐特殊性的论述也视为“诡辩论因素”来对待,这种表面上并不错的评价和判断,实际上掩盖着理论研究上的浅尝辄止。可以指出的是,虽然笔者在研究《声无哀乐论》之初,就已经听到“诡辩论”一类的轻率评价,但是迄今为止,还并没有看见一篇真正能在深入了解“声无哀乐”理论基础上,明确就其“诡辩论因素”做基本分析的文章。因此,似乎有必要说明,在不甚了解的基础上来做这样的评价,不仅于研究者无助,亦于学习者无益,其效果同理论研究中似是而非的判断没有什么两样。
以上六个方面的问题,均与对嵇康“声无哀乐论”思想价值的评价相关。当对嵇康《声无哀乐论》的研究已经有了大量成果的时候,就需要将这些经常隐藏在理论研究深层中的问题揭示出来,引起读者的注意,以利于理论研究进一步的发展。
❆
阿格里奇推送精选
来加入古典音乐群一起听音乐
扫码加入古典音乐群一起听音乐
扫描微信二维码⬆️⬆️⬆️即可申请加入
1、巴赫音乐欣赏群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