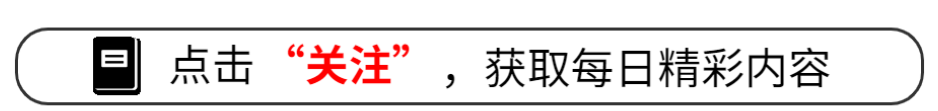张载对道家思想的吸收、消化及其影响——兼论宋明理学中的儒道因缘
张载对道家思想的吸收、消化及其影响
——兼论宋明理学中的儒道因缘
丁为祥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分别代表着两种源远流长的不同传统,也是中国一切思想得以发育的精神母体;而这种不同传统,也一如金银盾的关系一样,是同一中国文化之两个不同的侧面。正因为儒道两家的这种关系,因而只要一方遇到挑战,另一方也就必然面临相同的格局。宋明理学崛起时,整个中国文化就面临着这样一种格局;而早期的理学家,在其学术性格与思想体系中,大体上也都带有传统文化这两个不同的侧面,由此也就构成了理学崛起过程中的儒道因缘。
在作为第一代理学家群体的“北宋五子”中,邵雍(1011——1077)可以说是标准的人间道士,而周濂溪(1017——1073)的“烟霞气”连同其“窗前草不剪”的气象,[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参见程颢,程颐:《程氏遗书》卷三,《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页。]也与道家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只有到了张载,才堂堂正正地站出来,要求与浮屠老子“奋一朝之辩,而与之较是非曲直”。[ 张载:《正蒙·范育序》,《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5页。]从这一点来看,作为第一代理学家群体的北宋五子,也只有到张载时,才开始自觉地以“辟佛排老”标宗。——其实,这本身就是理学崛起过程中儒道关系的一种表现;更为奇特的还在于,张载虽然明确地以“辟佛排老”标宗,但其哲学中的许多思想因素也就直接源于道家。如此一来道家思想体系的根本,张载一方面固然表现了其辟佛排老之标准的儒家立场;同时又典型地体现着理学崛起过程中的儒道因缘。这样,从张载思想中辨析理学崛起过程中的儒道关系,也许更具有典型性。
但对于张载哲学,我们究竟应当从哪说起呢?在张载天人哲学体系所含括的天道观、人生论与理想指向三大领域中,其中哪一个领域都可以看出道家的思想因素,也都可以作出接近于道家思想谱系的诠释。但是,如果我们沿着张载哲学体系的展现逻辑而从其天道观开始,可天道观不仅要落实于人生论中,而且其天道观中的许多问题也只有在人生论中才能得到真正的证实;——如果孤立地就其天道观进行诠释,那么即使可以将张载解释为天文学家、自然哲学家甚或朴素实在论基础上的道德学家,却并不是张载本人的关怀。——因为张载毕竟是北宋五子中最先自觉地以“道学”来自我定位的理学家。[ 张载云:“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巽之谓孔孟可作,将推其所得而施诸天下耶?将以其不为而强施之于天下与?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于百姓,谓之王道可乎?所谓父母之心,非徒见于言,必须视四海之民如己之子。”参见张载:《答范巽之书》,《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49页。]不过,如果直接从其人生理想说起,虽然也可以较为简捷地辨析张载思想中的儒道因素,但这样的分析难免又存在着以理想裁定事实的弊端。如此看来,我们也就只能从其从现实出发的人生论说起了。
一、人生本体: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
从现实人生的角度看,张载(1020——1077)作为一个儒者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从其人生理论来看,则张载的儒家立场也同样是毋庸置疑的。但张载对人生的分析却并不是汉唐以来传统儒者的现实一层论,而是立体的双重人性论。如果说张载对人生理想的高扬既有儒家传统的因素同时又有对佛教超越性智慧相借鉴的因素,那么其对现实人生之多层面的照察与审视,则无疑又有来自道家的思想因素。——这又主要表现在张载对现实人生之根本依据——所谓双重人性论的论定中。关于双重人性,张载论述说: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焉者。[ 张载:《正蒙·诚明》,《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3页。]
这就是张载的双重人性论,对理学而言,它主要在于双重人性并建,或者说开辟了双重人性并建的规模,从而既揭示了人生的形上依据,同时又揭明了人生的现实基础,所以也就起到了把握现实人生之双重坐标的作用。因此,后来的朱子评价说:“此(按:即气质之性)起于张程。某以为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读之使人深有感于张程,前此未曾有人说到此。……故张程之说立,则诸子之说泯矣。”[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四张载对道家思想的吸收、消化及其影响——兼论宋明理学中的儒道因缘,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0页。]而朱子的弟子黄勉斎则评价得更为明确:“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恶,扬雄言善恶混,韩文公言三品,及至横渠,分为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然后诸子之说始定。”[ 黄宗羲:《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上,《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30页。]之所以说是“诸子之说始定”、“诸子之说泯矣”,首先也就在于其双重人性的并建对人生之现实表现与超越的形上依据之有机统一这一点上。
对于张载的双重人性,由于同时代的张伯端(983——1082)也有双重人性一说;又由于张伯端年长于张载三十余岁,且又在张载去世五年后的元丰年间才去世,所以人们纷纷推测说张载的双重人性论可能源自张伯端。比如侯外庐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首先提出了这一看法;[ 侯外庐:《宋明理学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以后孙以楷、李申等先生也同样坚持这一看法,比如孙以楷先生认为,“张载所谓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说法显然与道教思想有直接联系”,[ 孙以楷:《道家与中国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并且因为“其行文用语如此一致以及张伯端早于张载三十多年来看,侯外庐等人的推测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几乎可以断言,宋儒的天地之命(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说源于张伯端”;[ 同上,第206页。]李申先生也认为,“和张伯端相比,张伯端论气质之性,有道教的修炼理论为基础,又有一套详细而严密的论证。而张载此说,仅是择取要点而已。[ 李申:《气质之性源于道教说》,《儒学与儒教》,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在中国人性论漫长的发育历史中,一直存在着两条不同的线索或两种不同的传统,这就是“生”与“性”;而这种不同的传统,也就恰恰成为以后儒道两家的思想引线。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张载气质之性说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所以李申先生也明确指出:“气质之性说乃是道教修养理论顺理成章的发展。”[ 李申:《气质之性源于道教说》,《儒学与儒教》,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当然对于这样的看法,人们可能会辩解说其实孟子的“天性”思想本身也包含着自然之性的涵义,但“天性”毕竟不同于告子“生之谓性”的表达,也不同于庄子“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之完全自然化的表达。[ 郭庆藩:《庄子·达生》,《庄子集释》,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4年版,第658页。]当然,人们还可以辩解说既然如此,那张载为何还要批评告子“生之谓性”的思想是“人与物等”呢?[ 张载:《正蒙·诚明》,《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3页。]实际上,如果认真辨析张载的人性论思想,就会发现他虽然并不将人性归结为自然之性,但他也并不否定自然人性的存在,因为其“人但物中之一物”[ 张载:《语录》上,《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13页。]的说法本身也就必然包含着自然之性的涵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朱子何以会对张载的气质之性说有如此高的评价;而黄勉斎所谓的“诸子之说始定”也绝不仅仅是指从荀子、扬雄与董仲舒一直到韩愈这些汉唐儒生的人性论而言,而是指整个中国人性论探讨始终无法越出张载在融合儒道不同传统基础上所形成的双重人性论之理论规模与理论建构之外而言的。因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统一、儒与道的融合,实际上也就代表了中国人的整个世界;在此基础上,任何关于人性的探讨,既不可能越出儒道两家的思想传统之外,自然也就不可能跳出由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统一所体现的儒家本体与现象双重世界之外了。
显然,作为探讨人生本体的双重人性论,张载确实吸收了道家的思想因素,但又不能仅仅归结为道家思想。实际上,张载是明确地站在儒家立场上对道家观察视角的认可与思想观念之吸取、提炼与再表达,所以其双重人性的思想就既有道家的思想因素却又不能仅仅归结为道家思想。这一点,既是整个张载哲学的形成基础,同时也是理解其思想创造的一个基本原则。
二、理想指向:“民胞物与”与万物一气
如果说张载的人性论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关于张载的人性论,许多论者一直以 “二元论”来加以把握,意即其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是并重平列的关系,并由此认为这是张载哲学所存在的内在矛盾,所以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那么其以《西铭》为代表的人生理想论则可以说是众口一词、一致加以赞扬的论题。因为从二程起,就将《西铭》与《大学》并列,并作为洛学之入门书。大程甚至认为,“《西铭》某得此意,只是须得他子厚有如此笔力,他人无缘做得。孟子以后,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语”;[ 程颢,程颐:《程氏遗书》卷二,《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页。]又说:“孟子而后,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间语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尽近理。若《西铭》,则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说到道,元未到《西铭》意思。据子厚之文,醇然无出此文也,自孟子后,盖未见此书。”[ 程颢,程颐:《程氏遗书》卷二,《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7页。]总之,在北宋理学中,几乎没有人能够像张载的《西铭》那样获得大程的如此高评。大程去世后,小程继续表彰《西铭》,当程门弟子杨时对《西铭》的宗旨随意加以漫评时,小程又专门作了《答杨时论“西铭”书》,明确地以“理一分殊”作为《西铭》之大旨;此后,朱子也专门作了《西铭论》,继续阐发其理一分殊思想。明代以降,自吕柟编《张子抄释》起,就一直将张载的二铭(即“西铭”、“东铭”)作为独立篇章,置于整个《张子抄释》的篇首,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基本惯例。由此可见,就对后世的影响而言,宋明儒的文章几乎无出于《西铭》之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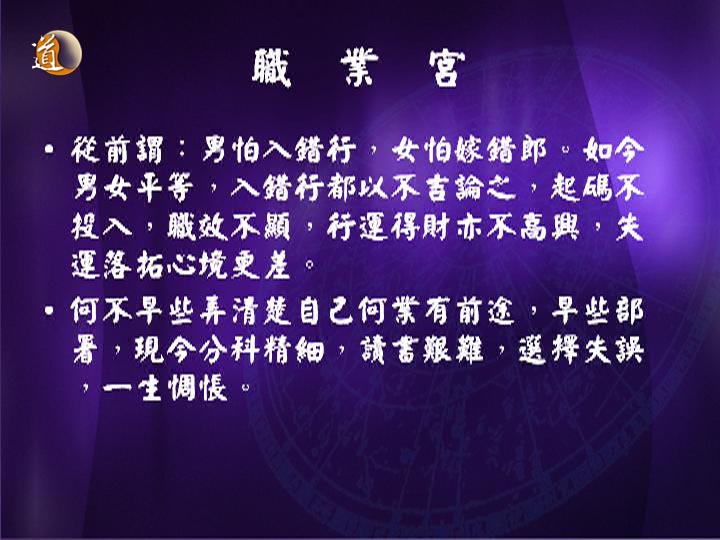
但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所以《西铭》作为张载人生理想之集中表达,其在理解上所存在的问题反而更大。关于宋明儒在对《西铭》理解上所存在的偏颇,尤其是程朱一系如何以其理一分殊思想“附会”《西铭》的宗旨,请参阅陈俊民先生的《张载哲学与关学学派》一书中的“‘理一分殊’非本旨”一节;[ 陈俊民:《张载哲学与关学学派》,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版,第109—114页。]但关于近几年国内在宋明理学研究中对《西铭》或张载人生理想所形成的种种误解,则需要我们依据张载本人的理论规模尤其是其思想中的儒道关系再加以辨析。
三、天道基础:太虚与气
关于太虚与气的关系问题,由于张载在《正蒙》的首章——《太和篇》中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由太虚,有天之名”的规定,[ 张载:《正蒙·太和》,《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9页。]而此一规定本身也就明确地显现着太虚必然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因而太虚与气的关系问题实际也就可以集中于一点上,这就是太虚的性质问题;如果太虚的性质得以澄清,那么太虚与气的关系问题自然也就会得到相应的澄清。
从这一诠释进路及其所展现的理论架构来看,张载其实就已经立体地撑开了儒家超越与现象两层世界,从而也就等于拉开了其从理论上与佛老“较是非,计得失”的主战场。在这一基础上,张载也就有了对佛老二教之基本立场的明确批评:
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故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从来,则深于《易》者也。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不识所谓有无混一之常;若谓万象为太虚中所见之物,则物与虚不相资,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为见病之说。……语天道性命者,不罔于梦幻恍惚,则定以“有生于无”,为穷高极微之论。入德之途,不知择术而求,多见其蔽于诐而陷于淫矣。[ 张载:《正蒙·太和》,《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8页。]
在这一批判中,张载首先对儒家的立场、观点作了一个基本的阐发,然后再依据儒家的基本精神展开对佛老的总体批评。那么,被张载明确地规定为“通一无二”的“有无、隐显、神化、性命”究竟是完全由现象所构成的一层世界呢还是所谓“形上形下一滚论之”?很明显,如果其前后项之间本来就是一层世界,那么张载也就完全没有必要用“通一无二”来规定其关系了;正因为其前后项分别代表着现实与超越两个不同的层面张载对道家思想的吸收、消化及其影响——兼论宋明理学中的儒道因缘,所以“通一无二”的规定才成为一种必须。因为还在这一论述之前,张载就已经明确地指出:“然则圣人尽道其间,兼体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矣。”[ 同上,第7页。]显然,在这一背景下,所谓“兼体”、所谓“存神”以及“死之不亡”等等,都说明张载用“通一无二”所规定的关系实际上也就包含着儒家现象与超越两层世界。
张载的天地、宇宙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而这种“天地”、“宇宙”,无疑既存在着气化流行的基础,但又绝不仅仅是所谓纯粹自然的气化流行所能说明的。这种情形,一如人虽然都是进化的产物,但却绝不能以猴子来说明人一样,更不能将猴子的动物性视为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所以,对于张载的天道宇宙论,我们也就只能以张载的方式,通过道德理性来理解、来说明,正像所有的自然秩序都已经被张载道德化为“天序”、“天秩”一样。与之相应,所谓太虚与气的关系,也只有在太虚的驾驭和主宰下,才能真正成为儒家所言说的天道本体及其发用流行的关系。
四、吸收与消化:张载哲学中的道家思想
到目前为止道家思想体系的根本,我们还没有正面分析张载与道家的关系,只是随着笔者对张载哲学体系的叙述,以随文点到的方式说明张载与道家确实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已。现在,当我们大体确定了张载哲学体系的基本规模时,其与道家的关系以及其对道家思想的吸收与消化,才成为一个不能不面对的问题。
那么在张载哲学中,究竟有哪些道家的思想因素呢?张载又是如何吸收、消化这些道家的思想因素呢?首先,张载哲学中确实存在着大量的气论思想,并以气之聚散来说明万事万物的存亡成毁以及人之得见与不得见的现象,这种以气之聚散说明万物存亡成毁的思想显然源于道家,尤其源于庄子。庄子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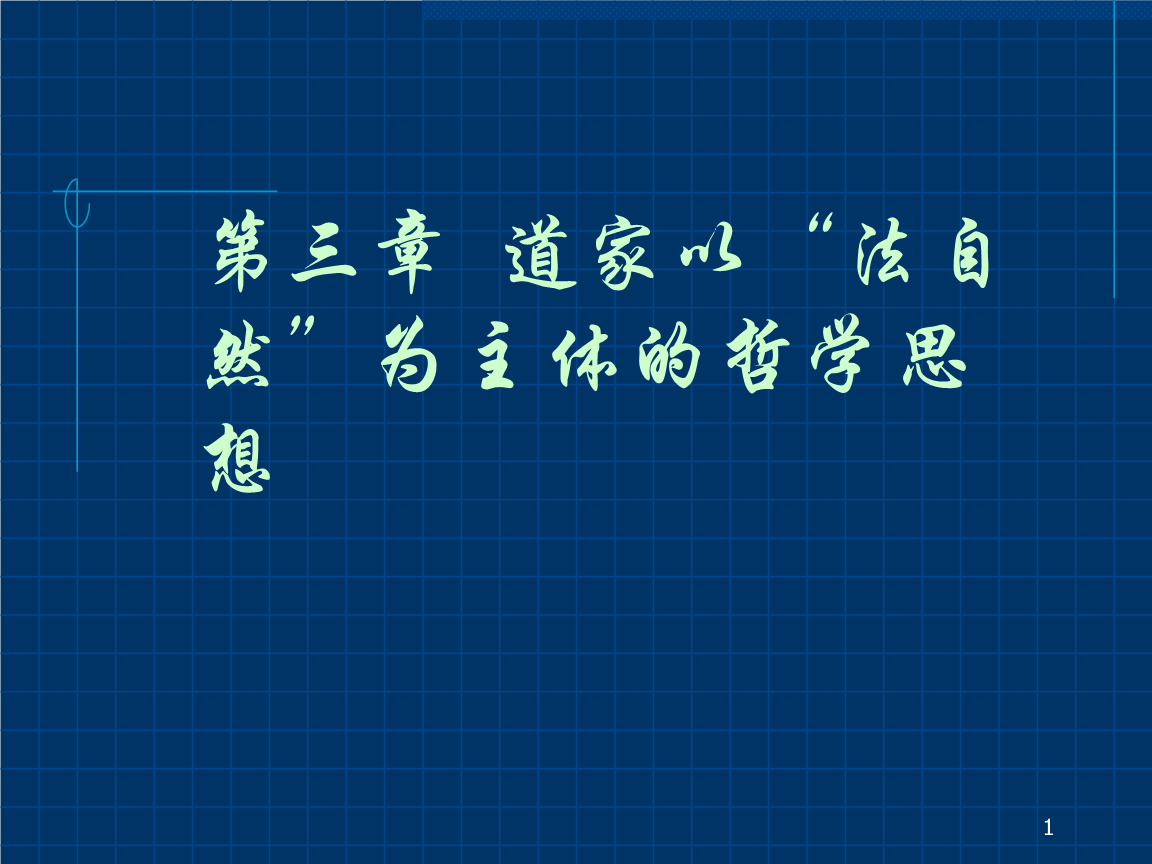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故曰“通天下一气耳。”[ 郭庆藩:《庄子·知北游》,《庄子集释》,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4年版,第733页。]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以“气之聚散”来说明人之生死的现象,所以张载完全作了继承性的吸取。因为在《正蒙》中,凡是谈到生死、成毁的现象,也都与气之聚散相联系,或者说就直接是气之聚散的结果。比如:“太虚无形道家思想体系的根本,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再比如“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途,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气之为物,散入无形,适得吾体;聚为有象,不失吾常。”[ 张载:《正蒙·太和》,《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7页。]还有如“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矣”等等,[ 同上。]也都是通过气之聚散来说明人与万物之生死存亡现象的。
“气”既然是从万物存亡成毁的角度引入哲学的,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将如何面对由气之聚散所构成的现实世界?在这一问题上,不仅儒道两家有分歧,而且老庄之间也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当然,这种不同也正表现着道家思想的发展。
如果从太虚落实于人生来看,那么所谓“虚者,仁之原”、“敦厚虚静,仁之本”、“虚心然后能尽心”、“虚心则无外以为累”、“圣人虚之至,故择善自精”等等,[ 张载:《语录》上,《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25页。]其实也都是对太虚之人生落实的具体说明。如果说太虚作为天德的人生落实就是至善,那么这一至善在人生中的表现又将如何呢?请看张载的如下描述:
有意为善,利之也,假之也;无意为善,性之也,由之也。[ 张载:《正蒙·中正》,《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8页。]
这就是说,作为天德、至善,太虚的人生落实必须达到“无意为善”之自然而然的地步,显然,这也就是庄子所谓“无心”之境界了。而其区别则在于,道家是由万物之自然存在走向人生之自然境界,所以他也就必须以“心斋”、“坐忘”作为实现前提,从而以人之“物化”的方式“同于大通”;也就是说,道家是不得不把人自觉地置于物的地位,——不仅以物之方式生存,而且还要以物的视角来面对世界。但儒家却完全是通过积极地参天地,赞化育之道德实践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境界的,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张载的“无意为善”正可以说是道家无心而又自然之境界的一种儒家移植。在这里,儒道两家之“无心”以及其表现之“自然而然”的特色是完全一致的,但又确实是通过不同的方向与不同的进路实现的。
(原文载于《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六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有部分删减)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